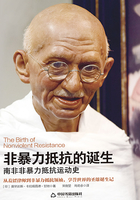
第十章 战后
1.往返印度和南非
1900年,布尔战争最重要的阶段基本结束。雷迪斯密斯、金伯利和马福金三地均已解围。科隆耶将军在帕阿德堡(Paarde-burg)投降。英军从布尔人手中夺回被占的英属殖民地,齐屈纳勋爵征服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剩下的不过是些散兵游勇。
当时我认为自己在南非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原打算只待一个月,结果却待了六年。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大致明确。可是如果印度侨民社团不情愿,我还是无法离开南非。我告诉同事自己有意在印度做公益性事务。在南非我学会了无私奉献,但我渴望有机会做得更多。此地有曼苏克拉尔·纳扎尔先生 、汗先生(Shri Khan),还有一些生长于南非,后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的印度年轻人,就目前情况看来,我回印度也没什么不妥。在恳切理论之后,我终于获准返回印度,(P.127)但前提条件是,如果此地出现任何意外状况需要我出面,侨团随时都可叫我回来,而我也要刻不容缓地返回。这种情况下,侨团会负担我的往返路费和我在南非期间的一切费用。我接受了这个安排,回到了印度。
、汗先生(Shri Khan),还有一些生长于南非,后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的印度年轻人,就目前情况看来,我回印度也没什么不妥。在恳切理论之后,我终于获准返回印度,(P.127)但前提条件是,如果此地出现任何意外状况需要我出面,侨团随时都可叫我回来,而我也要刻不容缓地返回。这种情况下,侨团会负担我的往返路费和我在南非期间的一切费用。我接受了这个安排,回到了印度。
我决定在孟买当律师,主要是想向戈克利取经,在他的指导下做公益工作,其次也是为了自谋生路。于是我租了几间房,开始有了一些业务。因为我和南非的紧密联系,光是从那儿回到印度的客户就很多,业务多得超过我的需求。可是我的这段日子一点儿也不平静。我在孟买才待了三四个月,南非就发来急电,说情况很严峻,张伯伦先生不日即将访问南非,要我务必出席。
我把孟买的办公室和家料理停当,就搭乘最早一班船赶往南非。那时已快到1902年年末了。我是1901年年底回到印度,1902年3月孟买的事务所才开张。南非发来的电报没什么细节。(P.128)我猜想是德兰士瓦出乱子了。不过我是只身返回南非,没带家眷,因为我以为自己四到六个月后就能返回印度。但等我抵达乌德班,听取了详情,大吃了一惊。我们中很多人都期待战后南非全境的印度人地位会有所提升。压根没人料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自由邦会有麻烦,因为战争爆发之际英国的兰斯道恩勋爵、塞尔伯恩勋爵和其他政府高官都曾公开声明,布尔人对印度人的恶劣待遇是战争诱因之一。比勒陀利亚的英皇代理机构曾多次告诉我,如果德兰士瓦成为英国殖民地,政府会马上替苦不堪言的印度人昭雪平怨。欧洲人也认为,现在德兰士瓦已是英国的领土了,就不会再执行原来布尔共和国针对印度人的法律。这一原则深入人心,乃至土地拍卖会也公开接受印度人的出价,而在战前印度人出价是没人接受的。于是很多印度人在公开拍卖会上买下土地,可是等他们到税务所申请登记土地转让契约书的时候,负责的官员竟然援引1885年颁布的《第三法案》拒绝登记!这一切我都是在抵达乌德班后才了解到的。给我说明情况的人还说,(P.129)张伯伦先生会先到德班,我们务必先要让他熟悉纳塔尔的情况。在那之后,我还要跟着张伯伦去德兰士瓦。
我们组建了一个代表团,在纳塔尔恭候张伯伦先生。在谦恭有礼地听完代表团申述后,张伯伦先生承诺他会与纳塔尔政府就代表团提出的意见进行磋商。我个人并不指望纳塔尔会很快修订那些战前颁布的法律。那些法律在之前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了。
正如读者们知道,在战前,印度人可以随时进入德兰士瓦。我留意到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不过不仅印度人受限制,欧洲人也一样。德兰士瓦的条件和原来差不多,因为之前布尔政府肆意占用了很多店铺里的存货,战后不少店铺还未重新开张。现在如果一下子跑来一大批人,市面上粮食和衣物供应就会紧张。于是我想,如果德兰士瓦只是临时限制人员出入,我们也没理由担心。只不过,欧洲人和印度人的通行证申办程序还是有点不同,对此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提高警惕。南非多个港口都设有通行证办证点,(P.130)欧洲人只要申请就能获得通行证,但对印度人的申请,却在德兰士瓦专门设立了一个亚裔人管理局(Asiatic De-partment)。这个特设的部门就是一个新动向。首先,该部门要求印度人向局长提出申请。局长批准申请后,申请人通常在德班或另一个港口拿到通行证。
如果照章办事,等张伯伦先生都离开德兰士瓦了我都别指望能拿到通行证。在德兰士瓦的印度同胞也无法替我代办通行证。他们没那么大本事。最后还是靠我在德班的关系弄到了一张通行证。我并不认识办证的官员,不过我认识德班市警察局局长,就请他陪我去办证点。他一口应下,还给我打了保票。我拿到了通行证,理由是1893年我曾在德兰士瓦住过一年,就这样,我到了比勒陀利亚。
比勒陀利亚的氛围明显令人觉得不祥。我看得出来,那个亚裔人管理局纯粹就是压榨印度人的阴谋诡计。管事的官员都是些在布尔战争期间跟着英军从印度跑到南非的冒险家,(P.131)他们留下来,为的是碰碰运气。好几个道德败坏,有两个甚至因受贿被起诉。虽然法官判他们无罪,但他们过后被开除了,明显是有罪。包庇袒护是家常便饭。当政府凭空设立一个单独部门,而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限制人们现有的权力,官员们自会时不时弄出些新规定,好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显得他们执行公务多有效率。这个亚裔人管理局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看出,自己的工作得从头做起。亚裔人管理局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我是怎么进入德兰士瓦的,也不敢直接问我。想来他们还不至于认为我是偷渡入境的。他们旁敲侧击地打听我是怎么弄到通行证的。来自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侨民代表团准备谒见张伯伦先生。要上呈的抗议书是我起草的,可是亚裔人管理局却不让我参加代表团。侨民领袖认为,如果我不能同行,他们就不该去。但我并不赞成这个想法。我和他们说,(P.132)我不会介意个人受辱,他们也不应在意;抗议书都准备好了,把它递交给张伯伦先生才是最要紧的事。于是代表团去晋见张伯伦先生。当时在场的印度律师乔治·戈德弗雷先生被委以朗读抗议书的重任。会晤过程中有提到我的名字,张伯伦说:“我已经在德班见过甘地先生了。所以我谢绝在此地再见他,这样也好从本地居民处直接了解德兰士瓦情况。”在我看来,他的这番话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其实都是亚裔人管理局教他这么说的,他们把在印度任职的不良习气都带到德兰士瓦来了。谁都知道,大英帝国的官员认为印度人狭隘无知。所以,住在德班的我怎么可能了解德兰士瓦的情况呢?亚裔人管理局的官员就是这么指导张伯伦先生的。但他没料到,我曾在德兰士瓦生活过;就算我没在那儿待过,我对当地印度人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眼下唯一关键的问题是:谁最清楚德兰士瓦的情况?当地的印度人既然不远万里把我从印度请到这儿,就已是做出了清晰的回答。(P.133)不过,有权有势的人往往听不进有道理的话。当时张伯伦先生既受他人左右,又急于讨好欧洲人,我们不可能指望获得他的公平对待。不过代表团还是去拜会了他,免得因为疏忽或担心有损自尊而错失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
我又一次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比1894年的那次还要艰难。一方面看来,张伯伦先生一离开南非,我就该返回印度。但在另一方面,我清楚地意识到,南非的印度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若自己是出于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大展拳脚的虚荣心回到印度,就违背了我所学到的替天行道的精神。我觉得,即便这意味着要在南非终老此生,我也必须留下来。直至云散日出,或不论我们如何极力抵抗,还是风云突变,把我们席卷散尽。我就是这么告诉印度侨民领袖的。就这样,和1894年一样,我表明自己要靠法律实务维持生计。我的决定正是侨民社团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