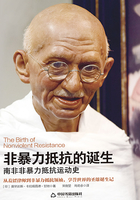
2.印度医护队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我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读者们切莫以为,提出此观点的仅我一人。在我之前很多印度人就主张我们应在此次战争尽忠职守。不过,现实的问题来了:战争的风声鹤唳之中,谁会聆听印度人细弱的呼声呢?我们提出协助英国人,将承担怎样的千斤重负呢?我们谁都没有扛枪打仗的经历,而战场上就算是非作战人员的工作也需要培训。我们连正步走都不会,(P.117)而肩背行军包长途跋涉绝非易事。除此之外,白人会把我们看作“苦力”,会羞辱我们,鄙视我们。我们该如何忍气吞声呢?如果我们志愿参军,又怎样才能让政府接受我们的请求呢?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必须竭尽全力让政府接受我们的请求;在实践中学会做事,只要有心,神必定赐予我们从军的能力;我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能否做好分配到的工作,只要努力训练自己就好;一旦决定参军,就坚持到底,不分工作贵贱,不管受何屈辱。
让政府接受我们志愿参军申请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过程曲折有趣,但此处就不详述了。简而言之,我们中的带头者接受了伤病员护卫培训,获得了体检合格证书,然后给帝国政府正式发函,提出申请。此信及信中我们欲报效帝国的热诚,乐于服从安排的态度给政府留下了甚佳印象。政府回信致谢,但还是婉拒了我们的申请。在此期间,布尔人不断推进,气势如虹,(P.118)英国人担心他们会打到德班。到处伤者成群,尸首成山。我们反复提出申请,最终政府批准成立印度医护队(Indian Ambulance Corps)。我们之前表示过,让我们去医院扫地倒垃圾都可以,而现在居然让我们组建医护队,大家自是高兴。刚开始,我们仅申请让自由的或契约期满的印度侨民参加,但我们也建议允许在役印度契约劳工参与。当时由于人手紧缺,政府就和雇主协商,让劳工也加入志愿军。就这样,一支庞大出色的印度医护队从德班开赴前线,人数将近一千一百人。动身之际,艾斯孔贝先生向我们表示祝贺,并为我们祈祷,读者们想必已经相当熟悉这位先生的大名了,他当时是纳塔尔欧洲人志愿者领袖。
英国各家报社都刊登了大幅报道。谁也没想到印度人会参战。一份英国人在某主流报纸发表诗歌,称颂印度人,诗中的叠句写道:“毕竟,我们同是帝国之子。”(P.119)
医护队有三至四百名前印度契约劳工,都是自由印度人努力招来的。自由印度人中有三十七名被视为领头人——递给政府的请愿书上签的是他们的大名,把大家召集起来的也是他们。这些人中有律师、会计师,有泥水匠、木匠,也有普通工人。从印度教徒到穆斯林,从马德拉斯人到内地人,不同阶层,不同宗教都有人参加。虽然商人多半未参加医护队,但他们赞助了不少钱财。部队的配给无法充分满足医护队的需求,而充足的必需品可以略为缓解军营生活的艰苦。印度商人为医护队提供了这些物品,还给医护队照料的伤员发放香烟糖果一类的小东西。只要我们在市镇附近安营扎寨,当地的商人就会尽力照顾我们。
加入医护队的契约工人仍受各自厂家派出的英国监工管理。但他们和大家干一样的活,也和大家住在一块儿,对此他们深感喜悦。(P.120)自然而然地,我们接手了整个医护队的管理工作。我们全体被称为“印度医护队”,印度侨团也因此获得赞誉。事实上,让契约工人加入医护队的是种植园主,功劳算不到印度人头上。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印度人,或者说整个印度侨团,由始至终对医护队管理出色,功不可没,布勒将军(General Buller)在战报中对此也予以肯定。
训练我们急救护理的布斯医生(Doctor Booth)也加入了医护队,担任医疗主管。他是位虔诚的牧师,虽然他主要在印度基督徒中事工,但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印度人也一视同仁。前面提到的三十七位领头人都受过他的培训。
除了我们还有一支欧洲人组建的流动医护队,我们一起共同并肩工作。
请愿的时候,我们未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但在接受请愿的回信中,政府批准我们不用上火线。这意味着军队常驻医护队要把伤员运到运离火线的后方。(P.121)怀特将军(General White)在雷迪斯密斯一役,伤亡惨重,野战医院根本应付不来。布勒将军组建临时医护队,就是为解此燃眉之急。在两军交战区域,战场和后方医院间根本没修路,根本用不了平常的交通工具运送伤员,只能靠担架抬。而战地医院通常建在火车站附近,和战场隔着七到十二英里。
我们马上投入工作,但其艰辛程度真是始料未及。日常惯例工作的一部分是抬着伤员走七到八英里。但有时遇上伤势严重的士兵和军官,就得抬着走二十五英里。早上八点出发,途中还要喂药,五点就得按要求赶到战地医院。真是很辛苦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要在一天之内抬着伤员赶完二十五英里。战争刚打响时,英军节节战败,伤员人数众多。(P.122)军官们不得已打消了不让我们上火线的念头。但必须说明的是,有此类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军官会告诉我们:按合同规定,我们可以不上前线;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承担风险,布勒将军也不会勉强;但如果我们自愿冒险,他们将不胜感激。我们原本就不想置身事外,早就想着要迎难而上,所以很高兴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们无一受伤,无一人挨枪子儿。
医护队有很多开心的经历,这里就不细说了。不过有一点得说清楚:我们和欧洲人组建的临时流动医护队以及欧洲士兵有很多接触,但是,没人觉得自己被欧洲人瞧不起,更没人受到粗鲁对待,包括我们中可能会被人视为缺乏教养的契约劳工在内。临时流动医护队由南非的欧洲侨民组成,战前他们都参加过抵制印度侨民的运动。但当他们知道印度侨民不计前嫌,对有需要的己方伸出援手,他们心软了。前面说过,布勒将军在战报中提名表扬我们的工作。(P.123)政府还向我们领头的三十七人颁发了军功章。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作战,布勒将军终于为雷迪斯密斯城解围。我们和欧洲人的医护队都被解散了。此后战争仍持续了很久。我们时刻准备着重新入伍,我们接到的解散命令上也说,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有需要,政府自会再次征用我们。
相较而言,南非印度侨民对此次战争的贡献并不显著。我们几乎没有人员伤亡。但诚心诚意愿对他人施与援手,必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如果对方压根儿没想到你会援手,他会愈发感激涕零。整个战争期间,欧洲人一直都很感激印度侨民。
在结束本章之前,有件事必须记录在案。雷迪史密斯城被布尔人包围时,城内除了英国人,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印度移民。除了几个商人,其他的印度人都是契约劳工,不是铁路工人就是英国绅士的仆人,其中有名劳工叫作帕布辛格(Parbhusingh)。城内指挥官给全体居民分配任务。最危险、最重责大任的活儿派给了帕布辛格,(P.124)因为他是“苦力”。布尔人在城外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架起了大炮,炮火摧毁了很多房屋,有时甚至炸死人。从炮弹打出炮膛到击中远程目标,中间有一到两分钟的间隔。城里被包围的人们如果能收到预警,哪怕只提前一点点时间,他们就能在炮弹落下之前隐蔽起来,躲过一劫。帕布辛格的任务就是坐在一棵树上放哨,在连连炮火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山头,一看到开炮的火光就敲钟示警。听到钟声,市内居民马上找掩护,躲开即将袭来的炮弹。
雷迪斯密斯城的指挥官盛赞帕布辛格做出的伟大贡献,夸奖他工作积极,从未漏敲过一次警钟。不消说,帕布辛格自己一直是命悬一线。他的英勇事迹传到了纳塔尔,最后也传到了时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 的耳朵里。勋爵赠给帕布辛格一件开司米长袍,还给纳塔尔政府写信,请他们举办赠礼仪式,大操大办。接到这个任务,德班市市长专门为此在市政厅组织公开会议。(P.125)这件事给我们两个教训。其一,不能轻视任何人,再卑微再不起眼的人也不能瞧不起。其二,再懦弱胆怯的一个人,到了考验的关头,也可能成就崇高的壮举。(P.126)
的耳朵里。勋爵赠给帕布辛格一件开司米长袍,还给纳塔尔政府写信,请他们举办赠礼仪式,大操大办。接到这个任务,德班市市长专门为此在市政厅组织公开会议。(P.125)这件事给我们两个教训。其一,不能轻视任何人,再卑微再不起眼的人也不能瞧不起。其二,再懦弱胆怯的一个人,到了考验的关头,也可能成就崇高的壮举。(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