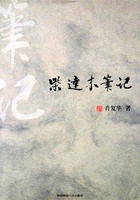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去摘星阁摘星星
四十年前,当我从北京走向柴达木时,怀里揣着的是一本李若冰写的《柴达木手记》。李老和诗人李季在1954年随第一批勘探队进入柴达木时,写的第一篇《啊,柴达木》的开头是这样三句话:
西去的路是荒凉的。一个人也看不见。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三句话三个句号,显现着作者当时苍茫和无奈的心情。
与荒漠寂寥共处已久的柴达木人,生活也是极艰苦的,我们队那时每月只供给两筒大肉罐头、两斤米、半斤油。但只要见到关内来的远方客人,便真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恨不得把家里的老底都翻出来:舍不得吃的大肉罐头、舍不得抽的双羊香烟、舍不得喝的肉冰烧酒……热情加豪情也要喝它个一地金沙、满目繁星……
柴达木五千年来的戈壁大漠是生命的禁区,“生命禁区”里,人的生命五十多年却一直在演绎生命的进行曲。当第一代外来的柴达木人繁衍出第一代真正的柴达木人时,柴达木鲜活了,生命了,成长了,茁壮了!不再为迎接客人缺吃少喝而抓耳挠腮了。当如鲜花盛开的菜肴摆满餐桌时,当你高举起青稞美酒时,两千年前那古老悠久的“子曰”拂面而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何青,《驼背父亲》的作者,作者认识她已二十四年。图为依然显小的何青
中午是小何青的私人宴请。我认识她已二十四年了,她个儿不高,不惑之年后依然长着一副娃娃脸,所以我总叫她小何青。二十四年前,报社办通讯员学习班,我要求大家写一篇自己最感动的人或事,在众多的文章里,有一篇让我眼前一亮:《驼背父亲》。《驼背父亲》是写她20世纪50年代就来到柴达木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我点评道:
这个“驼”字用得很好,使人联想起一生艰辛的父亲老了,背驼了,就像一峰“沙漠之舟”的骆驼,走过他们那一代人沧桑的岁月。这个“背”字也用得好,使人想起骆驼背上的驼峰,那是骆驼生命营养的源泉;也使人想起驼了背的父亲背负的责任与义务、奉献与无私……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小何青。小何青一贯为人真诚大气,她在基地找了一个有最大餐桌的饭店,请了十八个人,连刚大病初愈的“驼背局长”杨秀东也欣然而至。
杨局长从四川来到柴达木,一干就是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啊!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轮换调任了多少任局长?可至今仍守望着敦煌石油基地的仅有杨秀东一人了。老局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啊,你们又回来了!”
我说:“是啊,回来探亲了。过去,我们是从柴达木回北京探亲,现在,我们是从北京回柴达木探亲了。”
老局长有些激动:“柴达木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说:“我调走时局长对我说:人走了,把心留下……”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局长就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重重吐了出来。浓浓的烟雾顿时弥漫在他那凝重而沧桑的脸上,这使我想起了小何青写的《驼背父亲》。
老局长杨秀东当了一辈子主管生产的副局长,那时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柴达木油田战线又长,管生产的领导得腿长、嘴快、脑子不停地转,每天每时每刻都得把神经绷得紧紧的。
1979年,我从干了十二年修井工的野外队调到当时的局总调度室,杨局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天深更半夜,总调值班室电话急骤响起:远在千里之外的西部花土沟采油队天然气爆炸,有一家老小炸成重伤,生命垂危,急需总医院药物支援。我撂下电话赶紧给小车队打电话,打了七八分钟,无人接听。人命关天,可我初来乍到,一时竟手足无措,只好向杨局长直接汇报。杨局长听后干脆利索地做了三点指示:一、跑步去小车队找队长直接派车;二、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落实药物;三、不管多晚送药的车走后给我回电话。我不敢怠慢,抄起那一尺多的超长手电筒向小车队跑去。谁知队长家门前有一个修车用的地沟,一路急跑的我一头栽进那近两米深的地沟里。多亏了那超长手电筒,成了我掉下去时的唯一支撑物,使我至今仍肢体健全,可它却瞬间变成了残废。窝在沟底的我两三分钟没出来气,当我“哎哟、哎哟”的出动静时,队长已披着衣服出来四外寻摸:人在哪呢?
我说:“在沟里!”
队长把我拽了出来说:“这黑灯瞎火的,光听‘哎哟’不见人,我还以为狼来了呢……”
折腾大半宿,回到“总调”已是夜里四点半了,我不忍心再打扰杨局长休息,可转念一想,杨局长要是还惦念着这事,不是更睡不着吗?果然,杨局长还没睡,他叮嘱我和前线指挥调度密切联系,药一到马上汇报。
这就是我黑白记忆中的杨局长。

为欢迎四十年重返柴达木探访的北京学生,青海油田公司举办了官方欢迎宴会。图为作者与宗贻平局长(右一)举杯共祝油田明天更美好
晚上是油田公司的官方欢迎宴会,新上任不久的宗贻平局长和工会主席王志学来了。王志学第一个端起酒杯说:“你们是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自愿来到柴达木这个特殊的地方,并获得了‘北京学生’这个特殊的称呼的。今天,你们回家了,来,让我们为你们在柴达木所作出的特殊奉献,干杯!”
宗局长和大家一饮而尽后,又端起了第二杯酒,站起身笑着说:“要是按年龄,我应该叫你们大哥大姐了。”他的话一下就把大家“零距离”了。
宗局长的老家是河北的,可他却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柴达木人。1976年他走向油田,至今已整整三十二年了。当然比起“驼背局长”,他正年富力强。2004年我为写《天大的事》专程采访过他。那时他还是副局长,一直在开会,我就一直等他。当他一脸疲惫走出会议室,我和他聊起当年成立天然气公司的事时,他便和我一起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1995年那段难忘的岁月……

1964年,涩北气田的发现井北参3井气龙冲天,井场井架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图为当年涩北大火
那一年的元旦,是随着敦煌基地一场百年不遇的瑞雪纷飞到来的。局党委召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石油与天然气要两条腿走路,油气并举,以油养气,气为重点。并成立了局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天然气开发公司。第一任经理便是宗贻平。
三月初,他就带着两个人去涩北做前期准备。不久,一道指令像火一样燃烧在他的手中:投资2.5亿元,按期完成“涩北—格尔木”的输气管道建设和气田实验开发建设,在1996年8月31日务必将天然输至格尔木。这是一项硬性任务。他坐不住了,风风火火地带领一班人马,直奔涩北那仍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北参3井——这是涩北气田的发现井。1964年12月5日,北参3井怒发冲冠、气龙冲天,瞬间被附近帐篷里正在做饭的火苗点燃,井场顿时一片火海。几分钟后,钢铁井架便像面条一样化为铁水。
面对大火,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当时的涩北气田离现代化还太遥远。这一烧就是整整三十二年。粗算,烧掉人民币近三个亿。面对燃烧了三十二年的北参3井,宗贻平他们落泪了。他紧紧握着拳头像是在发誓:“伙计们,弟兄们,都看到了吧,烧了三十二年烧的都是人民币啊!烧得我们心疼心焦啊!我们一定要将天然气开发出来,送到千家万户去造福人民!”来自两千多万年前的天然气呼啸着、燃烧着……那是远古的呼唤、那是千年的祈盼,走近它、拥抱它,和它一起升腾、一起涅槃……
美国一家叫阿莫斯东方石油公司的专家曾考查过涩北气田和涩格管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完成这项工程需要两年。
是啊,没设施、没经验、没交通工具,只有一间100平米的二层小楼,既当办公室又兼卧室,挤不下的就睡地板。想想当年,1955年,十几条汉子,在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搭了几顶帐篷,垒了口大锅,修了第一条通往经井架的路,打了第一口石油探井,创造了柴达木的第一个石油奇迹。今天,我们仍要继续创造天然气的奇迹。自3月14日打火开焊以来,他们共用了五个月零十三天,便胜利完工了。
1996年8月31日,在格尔木举行的“涩北气田开发暨涩格输气管道工程投运”典礼上,宗贻平流泪了,一年多来,他仅回家不足二十天。没白没黑地跑在勘察的路上和工地上。困了,睡在车里;饿了,啃把方便面;渴了,喝口冰凉的矿泉水;没路,双脚去踏出一条路,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整日与风沙做伴,夜里与野狼共舞……他说:“真的,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真的,这条管道凝结着我们的汗水、鲜血和生命。”这凝结着他们汗水、鲜血和生命的天然气管道先后延伸到敦煌、西宁、兰州。今年(2008年),已直通北京……
柴达木几代人的天然气的梦想,终于像敦煌的飞天一样,自由地飞翔在天然气时代的神州大地上。
晚上十点多了,油田作家曹建川突发奇想,要我去一个梦都幻不来的地方——摘星阁。那是一个仿唐式的高大辉煌城楼。登顶,一地金沙的鸣沙山近在眼前。

鸣沙山,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南郊,面积约200平方公里,沙峰起伏,山如虬龙,宛若金山。图为鸣沙山月牙泉
月光余晖下的鸣沙山好似刚从月牙泉沐浴而出的“黄河母亲”,回首西望着自己的家园。我想,当年乐尊和尚西去东归时,在鸣沙山耳鸣黄钟大吕,眼观金沙佛光,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命和魂留在了鸣沙山和千佛洞。
如今,一千六百多年弹指而过,涅槃西天的哪颗星星属于他呢?抬眼望,满目繁星。捧一把金沙捂在胸前,心胸如大漠浩瀚辽远;摘一颗星星放在眼前,顿悟诗人顾城的那句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