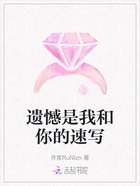
第2章 回忆总是酸涩
便利店外的雨幕像道透明的墙,将十七岁的蝉鸣与二十三岁的雨声隔绝在时光两侧。
林念在公交站台的雨棚下抖开速写本,潮湿的纸页上洇着半朵未画完的樱花,花瓣边缘是闫延围巾上的刺绣纹路。她盯着画纸发怔,指尖无意识摩挲掌心烫疤——那是十六岁那年,母亲发现她偷藏的漫画杂志,争执间打翻了桌上的搪瓷杯。
“念念,学画画能当饭吃吗?”母亲的话像块浸了冷水的抹布,至今仍能拧出刺骨的寒意。
作为小学老师的母亲总说,铅笔要用来写教案,而非涂满课本边缘的动漫人物。
直到初三暑假,她在少年宫画展上看见闫延的素描——画里的老梧桐树带着雨后的潮气,树皮纹路里藏着细碎的光斑,像极了奶奶家院墙上的苔藓。那时她才知道,原来铅笔能画出比阳光更温暖的东西。
父亲的工牌照片还夹在速写本里。泛黄的证件照上,男人穿着洗旧的蓝色工装,笑得比厂区的安全帽还要生硬。
自她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在外地修铁路,每年除夕回来,皮箱里总装着火车站买的劣质巧克力。十二岁那年,她躲在房间画火车轨道,被母亲撕成碎片:“你爸修了一辈子铁路,也没见把你带出这小县城。”
公交到站的提示音惊醒了她。便利店的灯光在雨幕中明明灭灭,像闫延手机锁屏里十七岁的自己——那时她总趴在课桌角落画速写,蝴蝶骨在校服下微微凸起,像只想要展翅的茧。
她忽然想起闫延刚转来班上时的模样:白衬衫洗得发旧,手腕上戴着奶奶给的银镯,说话时总习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他奶奶住在城南巷尾的老院子,”前世的记忆突然清晰,“青砖墙爬满紫藤花,夏天会结出紫葡萄似的花苞。”
闫延曾在写生时告诉她,父母在他六岁时去了深圳,寄来的电话卡比奶奶的皱纹还要多。直到高一那年,父母突然回来接他,说“深圳的学校更好”,却不知他在新课本里夹着奶奶手抄的《千家诗》。
雨小了些,便利店的玻璃门再次“叮”地打开。闫延的藏青色风衣还滴着水,手里多了份便利店塑料袋装的热奶茶,吸管上缠着樱花图案的纸套——是她从前最爱买的款式。
他站在雨棚边缘,像怕惊飞了什么似的轻声说:“你妈妈还是每天都去学校门口接你吗?”
林念的指尖骤然收紧。这个问题像把钥匙,打开了记忆里那间摆满教案的卧室:母亲总在台灯下批改作业,钢笔尖划过作业本的声音,比父亲电话里的忙音还要清晰。
她想起自己求了三个月,才被允许参加美术集训,条件是“每次月考必须进年级前二十”。而闫延转来的那天,恰好是她第一次拿到素描比赛奖的日子。
“嗯。”她接过奶茶,温度透过塑料袋熨着掌心的疤,“不过现在不用了,我高三了。”话出口才惊觉,这具身体的时间线停在十七岁,而她的灵魂早已在三十岁的画展上见过闫延西装革履的模样——那时他说“有些相遇是刻在基因里的代码”,眼底映着她挂在展厅中央的巨幅油画,画的正是城南巷尾的紫藤花老院子。
闫延的伞尖在地上画着圈,银戒在路灯下泛着微光:“我爸今年春节又没回来,”他忽然抬头,眼里映着便利店暖黄的光,“奶奶说,紫藤花今年开得特别早。”
公交在雨声中缓缓进站。林念握着温热的奶茶,看着闫延围巾上的樱花刺绣——那是她去年亲手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像极了他转学第一天送给她的带疤苹果。
原来命运早把他们的轨迹,织进了彼此生命的经纬:她在缺乏父爱的家庭里学会用画笔取暖,他在奶奶的紫藤花下懂得等待的温度,直到十七岁的夏天,两个缺了一角的圆,在速写本的纸页上拼成完整的圆。
公交车的尾灯消失在雨雾里时,她才发现奶茶杯上贴着张便利贴,是闫延的字迹:“城南巷尾的紫藤花,周末要不要去写生?”雨滴顺着纸边滑落,晕开“写生”二字的笔画,却让“城南巷尾”四个字愈发清晰——那是她前世画了无数次的场景,也是闫延藏着奶奶记忆的地方。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母亲发来消息:“九点前必须回家,别又去画室混。”林念望着便利店方向,闫延的身影正融进雨幕,围巾上的樱花刺绣时隐时现,像朵开在时光裂缝里的花。
她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自己在速写本扉页写的:“画画是为了抓住那些会消失的光。”而闫延,正是她笔下最顽固的光,无论重生多少次,总会在暴雨夜的便利店,带着紫藤花的记忆,照亮她掌心的烫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