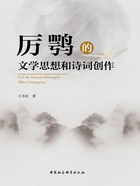
自序
此稿成于十余年以前,写得还比较稚嫩,然古人敝帚自珍之意,不忍舍之。今于文后附以已发表旧文数篇,有与恩师张兵先生合作三篇,以及独立撰写一两篇,合为一书出版,承载一段足迹,记录一段历程,也留下一段心路。
以厉鹗为“职志”的清代中期浙派诗人群体,在整个中国诗史上,只不过是惊鸿一瞥,难以引起人们注意;在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著中,至多亦不过寥寥数行。值得注意的是严迪昌、朱则杰二先生的《清诗史》以及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史》,于浙派诗人群体设专章介绍。又有张仲谋教授的《清代文化与浙派诗》,若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此著堪称目前研究浙派诗的唯一专书,而这书已经出版20年了。前人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此种情形恰如厉鹗在《宋诗纪事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宋诗“迄今流传者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佚无存,江湖林薮之士,谁复发其幽光”?三百年而后,我辈翻检浙派诸多诗人诗文集,感慨正复如此!就是作为此派领袖的厉鹗,至今尚无专书加以介绍。我书不足道,愿为引玉之砖!
以厉鹗为宗主的浙派士人,生前不屑仕进,功名不彰。生活于清代中期这样一个极度专制与文化牢笼之时代,不但是时代的悲哀,更为士人的不幸!此时正是文字狱案极度肆虐之时,心中纵有无限悲酸,亦不敢斑斑显言。这使得此派诗人在创作风格上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弹:心中江河激荡,流于文字反而波澜不惊,甚至干枯无奇。这点早为同时人所訾讥。然而当我们综合审视浙派诗人诗文集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了然于心、心照不宣之感。浙派诗人摄于王朝之威,在貌似平淡无奇的语言间建立了一套彼此心意相通的暗语系统。想想厉鹗友人王豫横遭文字狱案牵连入狱,其妻弟姚世钰日夜惊惧,厉鹗与王豫、姚世钰交谊均非泛泛,此时他正流连于杭、扬间,表面上看,人如平素,诗仍惯常,但真的是这样吗?
“知人论世”的说法由来已久。对于浙派诗人来讲,诗歌创作实为第二层面的事情了。据目前可以考索的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属于浙派诗人群成员的几有百人之多。这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十分松散的群体,有悖于向来对于诗歌流派认为创作倾向、创作风格等为基本判定因素的看法,这一诗人群体其实尊尚宋调者固比比皆是,追步唐音者也不乏其人,折中唐宋并不鲜见,自抒性情、不问尊尚的也大有人在。诗学尊尚如此迥异的这一群体,是靠什么走到一起来,结成深厚的情谊,以至于两三日不见,辄“相思不已”,书信往还,靠的是相同或相近的人格与价值取向。借用目下一句流行语:这是一群“三观”十分接近的人。不管他们来自何种背景,曾经有过何种跌宕起伏的人生,现在他们聚首一处,没有尊卑高下之分,谈诗论艺,切磋学问,隐然是风雨时世中自成一体的群落。因此,对于浙派诗人群体研究来说,其诗实为其人的佐证,人第一,诗第二。这里丝毫没有忽视浙派诗歌创作独立价值的意思,笔者想说:研究浙派诗人群体,应以其诗印证其人,深入了解并理解其人之后,对其诗才可能有准确客观的评论。否则,在对于浙派诗歌创作的评价上,则可能隔靴搔痒,流于表面化。
为了对于浙派诗人群体有一个全面的研究,对其在清代诗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此派宗主厉鹗是一把“钥匙”,加以较为全面研究首当其冲。十余年过去了,在此书之后,六十万字《清代中期浙派诗人集群研究》也已成稿。其中甘苦,冷暖自知。虽然,笔者的浙派研究尚“在路上”,笔者的理想状态是打通浙派诗群初期、中期、末期研究,成一《浙派诗人群体流变史》,则不枉“以码字讨生活”之名矣。
王小恒
丁酉冬月于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