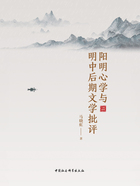
绪论
明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期,明代前中期和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师古与师心的较量中前行,文学批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代前中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推行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控制了士人的思想,成为普遍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学术思想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对当时理学盛行带来的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缺乏思想个性和创造力的做法不满的,先是陈献章,继而是王阳明。王阳明在陆九渊、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创立心学的思想体系。心学实为理学的别支,在根本原则上与程朱并无区别,但程朱以“理”为客观,故须博学、谨守;心学则以“理”为主观,所谓“心即理”,所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肯定并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具有思想解放的倾向。心学的出现,无疑是明代思想文化由“尊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同时又加剧了这一转变趋势。至嘉靖、隆庆之际,王学左派如王畿、王艮及其后学又时时越过师说,把“心即理”发展为“欲即理”,尊重个性、肯定人欲的自然人性思想在当时已被普遍接受。思想界长期以来独尊程朱、专制而僵化的局面被打破了。由此,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明代文学批评是宋元文学理论批评的惯性延续,却又将其中所潜含、积聚的矛盾、新质异常醒目地凸显出来,因而具有明显的多变性、复杂性。其间既有雅、俗文学势力的升降变迁,又有雅文学内部尊古与师心两种思想的对立递嬗。
从时间上看,嘉靖、隆庆之际为一大枢纽,此前以诗文批评为主线,且以复古思想为主导;小说戏曲批评则相对寥落、沉寂。此后文坛局面巨变,通俗文学方面开出新局固不待言,雅文学领域亦出现新变,一扫往昔尊古尚雅的习气。而雅、俗文学批评同时并存,互相影响而又分途发展。介于二者之间的嘉靖、隆庆时期,尊古与师心,尚雅与尚俗呈胶着状态,是为过渡期。而至明末则又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综合趋势。显而易见,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轨迹,与明代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大致同步,具有无可置疑的对应关系。每一种文学思潮的产生无不与哲学思想的新变息息相关,而文学思想的新潮又会融入哲学的洪流,二者互为推动力,使哲学和文学两种领域的思潮互为影响,交叉并进。由于明代前期和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内容和走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考察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阳明心学的确立可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明中期以后文学批评的走向。
一
阳明心学和明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受到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的研究者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阳明心学的研究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研究者不但把阳明心学作为研究本体来加以考察,更是以阳明心学作为哲学背景考察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关系。特别是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深受研究者的关注。明代心学的产生以及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使明代文学批评显现了异于以往的特征。一是纵向比较方面,总体而言,明代在批评的方法、对象、范围等方面开拓出较宋元更新、更宽的格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宋元还初露端倪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此时已发展壮大,与诗文理论共同构成了明代诸体文学批评的完整体系。与此相应的是,文学评点逐渐成熟,成为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之中的重要形式,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理论财富;二是在明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身态势方面,明代文坛有一个突出特点:流派林立,异说纷呈,显现出一股新思潮,强调文学源于人的心灵,充分体现人的个性,主张任性而为,在文学批评上集中体现为童心说、情真说和性灵说。因此研讨哲学思潮如何作用和反作用于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在这种作用下明代文学批评的内质和表现特征如何,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的命题。
心学背景下,明代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程华所说:“一方面,它表现为文学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它又被文论家用一定的哲学观和伦理观加工整理后,上升为系统的文学情感的理论,构成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1]文学批评中对文学情感的重视,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反映。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在心学家、文学家的群体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与人类的情感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学创作实践彰显了此时期情感的活跃和个性表达的特点,此前文学的“言志”功能和“缘情”功能经历若干变化和发展后,在此时的创作实践中被更多地张扬开来,从先秦就受到儒家关注的情感理论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论题之一,情感理论内涵的继承和变迁成为明代诗学逻辑进程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一。
由宋到明,文学情感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宋明理学昌盛,具有健康、合理内核的儒家文艺思想走向了极端,文学创作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情感钳制,文学情感理论具有鲜明的理学特征。明代中叶,以李贽为中坚的思想集团上继先秦、魏晋,掀起了一股反传统的强烈的浪漫思潮,在情感思想上,“理”的规范逐步解体,李贽提出“童心说”,汤显祖倡导“为情作使”,袁宏道力主“独抒性灵”,文学情感理论的抒情性更加彰显。其二,宋代诗坛“尚理”,好以议论为诗,北宋末江西诗派诗风盛行,在诗歌的情感内容上一度偏离了诗艺的美学特征。严羽提出吟咏性情的主张,其文学情感思想影响到明清两代。
从上述对文学情感理论发展轨迹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明中叶以后文学情感理论的内涵发生了转变,主情思想成为其文学情感理论的主导思想。对此时文学情感理论的代表人物徐渭、李贽、汤显祖等的文学理论的解读,对主情思想体系的确立、发展和影响的阐释会起到关键作用。除了政治的影响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外,阳明心学为明中后期文学情感理论提供了发生的哲学背景和发展的适宜土壤。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代文论中情感理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代抒写性灵、表现个性的文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文学情感理论从早期的感物说向晚期的性灵说转变的关键。
正因为阳明心学从产生以来,一直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心学与文学、心学与文论的研究就有了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清晰的理论内涵和框架,到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前期与中后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特点,中后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更强调自我和自适,更推崇个体和个性,更注重表现和审美。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既有政治社会的原因,也有哲学思想的影响,还有文论自身的发展完善,其间,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批评的文学观、文体特征、美学特质、话语特色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个问题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会为明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找到一个较新的角度,对于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的认真梳理和论证,也会有助于从哲学、史学和文学相融合的角度丰富对明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研究,同时扩大文论解读的研究方法和视域。
二
20世纪以来,对于阳明心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无论是对阳明心学的哲学思想研究,还是美学思想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对心学的研究著作数量较多,代表著作有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在对王阳明心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境界的视域对心学进行论述,观点较为深透,他认为:“王阳明哲学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熹哲学的反响,他倡导的‘心学’是在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具有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是北宋以来理学扬弃佛道,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的一个结果,在整个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2]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也较具有代表性,除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体系化的解读外,还对王学的终结及对近代哲学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则把王阳明心学放在理学的背景下,从理学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了心学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蔡仁厚的《王阳明哲学》、李书增的《中国明代哲学》、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等也都从不同的视角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阳明及心学在国外也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更大,对其的研究也因此很盛行,我国翻译出版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包括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和冈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等。冈田武彦的《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对明代的文化、明学的源流进行了考察,对王门三派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总结,以宋、元、明、清整个思想文化发展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论述了王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而细致地论述了王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对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明末其他儒学派别进行了比较。
对心学家的文学成就进行研究在20世纪上半期比较普遍,包括对王阳明的诗文创作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前,文学批评史对王阳明心学这部分的提及更多的是把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文学,特别是明中后期文学发展变化的哲学背景来论述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的研究视野更加宽阔,伴随着此时期美学研究的兴盛,对王阳明的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逐渐增多。对于阳明心学代表性人物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比较广泛,特别是王学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是心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所以文学思想本身就融入了心学的理念,把这些人的心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如左东岭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其论述深透的部分是“李贽的哲学思想”和“李贽的文学思想”两章,但作者没有单就李贽的文学思想本身立论,而是将其放在时代的交叉点上,透视其人格心态、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的特征、成因及其影响。这种文、史、哲交叉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他在另一部著作《王学与中晚明世人心态》中,结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诗文创作实践,对王阳明的求乐自适意识及文学审美情趣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黄卓越在《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中,对阳明心学的出现与前七子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关系加以论述,认为:“正德时期的各种变化,意味着当时整个士林之精神状态正处于极度的沉寂与压抑,落入到精神的谷底,由此,新的转机也在孵育与酝酿之中,从完整的氛围看,无论是新兴的道德主义理学,还是阳明等的心性之学、良知之学,均是为解脱沉重的精神危机所做的不同努力,而审美主义则于此强劲的精神蜕变中反显得不适时宜,甚至被看作是此集体拯救过程中身心堕落的标志。”[3]另外,还有张晶的《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陈少明《白沙的心学与诗学》等,对心学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研究也较有代表性。
对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也是一直以来研究的主要维度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潘运告的《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宋克夫、韩晓的《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与万历时期文学概观》,黄卓越的《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等,都关注了心学的本体和内涵对于文学思想形成和转型的影响。其中许总和马积高的著作影响较大。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选取一个新的角度——“近世化”的背景来重新审视宋明理学及其文化影响,把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分化、衰落过程中对文学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进行了论述,其观点是:“理学注重的是性理之学,文学则注重情文之美。但是,在宋代开端的文化‘近世化’进程中,理学与文学形成了交流与沟通,理学家借文化以传道明心、文学家重理而文以致用,而文人往往集学者、文士于一身的现象,更直接推进了文学与理学的融构进程。”[4]
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则从理学与文学的外部关系的角度进行阐发,其中既有宏观的梳理,如整个明代前期的理学在文学发展中的负面作用的阐释,也有微观的论证,如明代中期的反理学倾向、李贽反理学思想等,视域开阖自如,其对理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十分清晰独到,在书中马积高把二者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从北宋后期起到南宋末年以前止。这一阶段以程学与苏学的斗争揭开序幕,中间经过江西诗派与理学的暂时结合到朱熹大力攻击苏学结束,文学家渐渐地归附理学,但这种归附往往是皮相的、口头的。与此同时,理学家亦渐渐地改变其轻视文学的态度,虽然有的人(如朱熹)还弹着‘作文害道’的老调,实际上包括朱熹在内的一些理学家都在通过评文、选文,企图用理学的标准来指导文学的写作。”[5]“第二阶段,从南宋末年起(在北方则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到明朝前期(弘治以前)止。认为这是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时期。但朱熹、陆九渊以后,理学的发展也停滞了。此时的一些文学家,论文力图将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论诗则随着所处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对儒家传统的诗教作出自己的解释,有的强调怨刺,有的强调温厚和平,不拘守宋代理学家只求温厚和平的一格。”[6]“第三阶段,从明代中期到明末之际止。这是王阳明的心学从兴起、发展、分化到衰落的时期,也是文学上的反理学思潮由孕育、发展到趋于低沉的时期。”[7]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核心理论与心学关系,包括以本色论、童心说、性灵说为例,来论述性灵文学思想的发生、内容、表现等。
明代各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不断涌现,对这些文学流派及思潮的研究也成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研究的热点,如对唐宋派的研究、对童心说、性灵说的研究等。其中,廖可斌的论文《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把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研究,观点较为系统,较具有资料性。黄毅的著作《明代唐宋派研究》则从唐宋派的文学理论、地位和影响、作家个案研究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述,其中对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是对唐宋派进行研究的专著,但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李贽及其童心说一直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对象,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各种版本的《李贽年谱》成为一般研究者的参考,其中容肇祖的《李贽年谱》、黄云眉的《李卓吾事实辩证》、林海权的《李贽年谱考略》、林其贤的《李卓吾事迹系年》,被认为比较具有权威性。此外,各种文学批评史中对李贽其人及思想、文学成就、文学理论都有涉及,特别是对“童心说”的评价各有精到之处。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中把童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联系起来,认为童心就是市民之心;张少康认为童心是最纯洁、最真实的,李贽的童心说为“文艺新思潮奠定了哲学政治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8]。袁济喜在《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把李贽的“童心”与老子的童子之心对应起来考察,认为老子之心是排斥人欲的,而李贽的童心是人的私心,是带有工商市民色彩的童心。
对公安派的研究近几年来成果也比较多。黄卓越的《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把情感和性灵作为晚明文学思想进程中的一对内在矛盾进行研究,对性灵概念的追述及两种性灵说的分辨比较有新意。范嘉晨、段慧冬的《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则是对性灵文学的专论,以性灵文学作为主线,对公安派及性灵说从纵向的流变到横向的主张都进行了论述,但其对阳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关系没有进行较多的阐发,只是概括地表述为其思想形成受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特征的影响。总之,对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潮的研究如今已走向了立体和深入,研究成果颇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大都从这样几个维度来研究:
文学情感的流变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情感的生成及在各阶段流变的特点和内涵,这个维度史的脉络清晰,资料性较强,代表观点有:孙蓉蓉的《论古代文论中情感论的流变》(《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以情与志为线索,重点探讨了先秦、魏晋和晚明时期情感论的流变特点,并用这三个时期的创作实践加以印证,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情感理论在各个历史时期批评家们的认识、观点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差异很大,但在情与志、情与物相统一与融合的问题上,批评家们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此外还有庞学铨的《中国古代情感理论的特点》,把中国的情感理论与西方的情感理论进行对比,认为“在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情感理论,荷马的诗篇以神话的形式表达了情感的客观意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9]。这篇论文在中西对比方面的资料和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篇论述情感理论的论文是程华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情感理论的特点》(《广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阐述了“言志”中心与情志并举、从“诗缘情”到“为情造文”、从情志并重到理性钳制的观点,并结合李贽、袁宏道与袁枚的文论和创作,阐释情志的变化和融合是情感内涵特征的观点。
文论家个体文论思想研究。左东岭的《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认为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公安派与汤显祖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变化较为明显的一环。左东岭的另一部著作《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则把李贽的文学思想放在晚明这个历史背景中考察,把他哲学观的形成与晚明文化的浸润联系在一起,因而其观点能从宏观入手、微观阐发,论述有一定的深度。此外,易闻晓的《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刘尊举的《唐宋派文学思想研究》、陈晓艳的《袁宗道文学研究》、张建业的《李贽与公安三袁》等论文也对这个时期文论家的个体文论思想进行了阐发,这个维度的研究数量很大,且大部分研究较有深度,涉及对明代主要文论家的文学情感观的论证和思想背景研究。
审美研究。从审美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文学情感理论进行解析,观照了反理学意识、生命意识、主体精神、文学实践方面,从审美(美学)这个大范畴来研究,如王刚的《生命情感的言说与主体精神的成长》、崔秀霞的《从“性灵”到“尊情”》、窦传美的《论李贽美学思想中的生命意识》、邓新华的《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大多是对明代文学情感理论中的美学特质进行轮廓式研究,是从外围入手研究明代文学批评中审美理论的角度,这方面的研究尽管有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角度和视域还不够开阔,对明代中后期文学审美理论本身的挖掘式研究成果不够丰富,特别是对心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进行审美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够。心学思想之中很多是具有审美素质的,而心学思想所拥有的审美品格,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明中后期的文学批评在审美领域的影响如何,这些层次的研究目前展开得不太充分,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此外,对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综合研究,这一类研究数量上较多、综合性较强,需要筛选和判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胡建次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兴感论》(《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在黄卓越的《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对唐宋派的文学理论及情感与性灵这对晚明文学思想进程中的内在矛盾的解读很到位,认为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地达到令学术界满意的程度,许多研究者把“情感”和“性灵”看成是一个概念,因为都与主体心理相关,且具有反义理的取向。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判,正是这种概念相互间的摩擦、吸引,甚至重组的过程,构成了晚明文学的内在矛盾及由这些矛盾引起的观念变迁,因此作者从二者关系角度深入开掘,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中晚明文学思想裂变的哲学动因及反映到文学实践中的文学创作表现。
三
尽管在心学与明代文论的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著述已为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在当下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下,笔者认为此选题方向还有可深入探讨的必要和空间,主要体现在阳明心学的核心与明代以童心说、情真说、性灵说等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个问题上,其中对阳明心学如何影响明中后期文学审美观念的变革、审美内涵的转换,以及审美范畴的确立这个维度的研究不够,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本书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本书以阳明心学和明代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梳理明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明中后期的文学批评的变化及表现进行整理和提炼,引入阳明心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审美论,建立心学和明代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学理关联,为深入研究明代文学批评打开一个视角。通过分析、论证和研究,最终达到清晰解读阳明心学与明代文学批评关系的研究目标。
运用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阅读有关阳明心学及明代文学批评和创作的相关著作,阅读代表性的心学家及文学家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通过个案研究把握理论的核心,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研究方法,系统地整理文献,提炼观点,做到理论阐释观点明确、论证清晰。
运用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法,对心学家和文学家的文献记载要充分阅读,涉及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要重点了解,对文学领域的相关著作更要研究透彻,力争很好地完成这个涉及文、史、哲三个领域的研究论题。
[1] 程华:《中国古代文论中情感理论的特点》,《广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4]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上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5]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7] 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8]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9] 庞学铨:《中国古代情感理论的特点》,《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