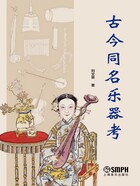
前言
古今乐器因其演奏方式、形制结构、使用材质、共鸣发声等因素的相同或相似有时具有同样的名称,但其本质却并非为同物。同名乐器在不同历史语境、不同文化生态、不同用乐类型中有不同的所指,进而在相关乐器文化传播中,以相对稳定的本域音乐文化圈审视、判断、界定与命名外来输入乐器文化名物时,造成与本域音乐文化圈以及传统历史文化中乐器名称的混淆。随着外来输入乐器以及新起乐器在本域文化圈中交流传播的不断扩大,其乐器定名又趋于稳固和逐渐的统一,此即在世界音乐文化范围内形成的乐器同名异实现象。本书以同名乐器名称为中心,对同名异实乐器在发音原理上的异同表现进行细微的分析与阐述,对造成乐器同名异实的缘由进行分析与总结。
一、乐器存在的同名异实现象
历经数千年的漫长音乐历史发展,世界乐器种类丰富、品类繁多。源远流长的乐器历史是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亦是古代音乐文化先进水平的重要见证。
回溯音乐历史,有同名异实乐器者,即乐器具有同一名称,但并非为同物。闻其名更要考其实,以下以同名异实乐器存在的现象关系考索为视点,分十一部分对同名乐器的缘起、同名表现以及异实区别进行梳理与阐释。
1.《律吕正义》载:“民间有铁叶簧,削锐其首,塞以蜡蜜,横之于口,呼吸成音……即今之口琴也。”[1]同为记载清典章史料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亦有载“口琴”,其云:“口琴,用铁,一柄两股,中设一簧。柄长三分,鼓长二寸九分……横衔其股于口,以指鼓簧转舌,嘘吸以取音。”[2]并附之以“口琴”图(见图1)。
可见,此载口琴与今普遍所称的西来之口琴(见图2)并非为同物。明《谷城山馆文集》、《东西洋考》、《汲古堂集》,清《西域图志》、《奁史》、《焦轩续录》、《新齐谐》、《清通典》、《清礼器图式》、《清史稿》、《大清会典图》等诸多文献均有录此类“口琴”,今反而多以“口弦”为之名为其所称。
2.《清朝续文献通考》有载“大提琴”,亦非今所称之的西洋弦乐器类大提琴(见图3),如其文云:“大提琴,长三尺,槽大六寸,八角形,柄上有挺弦,可升可降,弓用马尾,百二十茎。”[3]文载之余亦有“大提琴”附图(见图4)。可见,古今“大提琴”同名却并非同器。
3.另如“箫”名之乐器,今多指单管竖吹的竹制气鸣乐器(见图5)。但在古代,箫指由多管按一定音列排列组成的排箫。如《文献通考·乐考十一》载:“箫,凡十八管,取五声四清倍音。”[4]箫的多管排列数量有以十管、十六管、十八管为多者。如《隋书·音乐志》有载:“箫十六管,长二尺。”[5]《宋史·乐志》亦载:“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6]后又续曰:“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7]《元史》亦有载:“箫,编竹为之,每架十六管。”[8]另如《大明会典》《律吕精义》等均有载[9]。
多个长短有别的竹管编列而成,可以充分看出箫实为今所云“排箫”乐器,如《文献通考》载:“箫之为器,编竹而成者也。长则声浊,短则声清,其状凤翼。”[10]《文献通考·乐考十一》无载箫图,陈旸《乐书》在论箫文同时,并附“十八管箫”之图[11](见图6)。
可见,同为“箫”之名,实有多管与单管“箫”器之区别,即今称排箫与箫之别。《朱子语类·乐》中对其亦有辨别,云:“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云‘箫’方是古之箫,云‘箫’者,排箫也。”[12]另如清初深谙诗词与音乐的纳兰性德亦是有察多管古“箫”与单管洞箫之别,在其所著《渌水亭杂识》有载:“古之箫,即律管也,三十六律管,长短作一排……今之箫,乃古之龠,名异而体同。”[13]今按龠箫有异,纳兰性德所云龠箫“名异而体同”,其真伪此处暂且不论,但纳兰性德却明显注意到同为“箫”名,却有古今箫多管与单管在形制上的显著区别。
4.今所名腰鼓多指鼓身两端略小于中间,演奏时挎于腰间,双手各执槌敲击的膜鸣乐器(见图7)。但在古代,腰鼓多指鼓体腰部细于两端的一类膜鸣击奏乐器。如《通典·乐典》载:“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腰。”[14]《文献通考·乐考十一》亦谓腰鼓“大者以瓦,小者以木类,皆广首纤腰,宋萧思话所谓细腰鼓是也”[15]。另如《信西古乐图》中的腰鼓绘图(见图8)[16]。可见,古今腰鼓同名却并非为同物。
5.今所称手鼓者,多指维吾尔族音乐使用中鼓体呈圆形,又称“达普”“达甫”“达卜”或“达夫”,即单面蒙以皮革的拍击膜鸣乐器(见图9)。如《清朝续文献通考·乐考十三》云手鼓为:“回部乐:凡筵燕,回部司手鼓一人,即达卜。”[17]如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手鼓即指此乐器。
但在古代,手鼓多指鼓体附加构造有柄可持者,如明·王圻《三才图会》云:“手鼓,其制扁而小,亦有柄,令歌者左手抁,而右手击之”[18],并有附图(见图10)。《清史稿·乐八》中对此种手鼓的形制有更细致的表达,云:“手鼓,木匡,冒革,面径九寸一分二毫,腰径一尺二分四厘。以柄贯匡,持而击之。”[19]如上所述均是与今所称手鼓有别的有柄手鼓历史用乐记载。除此之外,《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律吕正义后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均有载此种手鼓。
可见,同名为“手鼓”,乐器之实并不相同。其区别主要体现在手鼓的乐器构造与手鼓的演奏方式上,即主要区别在于单面抑或双面蒙皮、有无持鼓之手柄,演奏在于拍击还是杖击。
以柄贯匡且可持柄的手鼓如今在不丹、尼泊尔以及我国藏族、蒙古族等地区宗教仪式中仍有使用。圆形可持柄与圆形无持柄一类的手鼓名称乐器,较好地体现了乐器同名不同器之现象,亦体现出了不同生态文化乐器名称的原本状态、固有称呼以及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内涵。
6.今天所称呼的胡琴类乐器多指以二胡、京胡、板胡等组成的拉弦乐器。如《清史稿·乐八》载:“胡琴:二弦,竹柄椰槽面以桐。槽径三寸八分四厘,为圆形,与笳吹之胡琴椭而下锐者不同。山口凿空纳弦,以两轴绾之,俱在右。弦自山口至柱,长二尺三分五厘二毫,以竹弓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20]此载史料价值颇高,其所述两次“胡琴”乐器名称,亦代表两种不同的“胡琴”之实,即竹柄、二弦、槽以椰制、面以桐制之胡琴与“椭而下锐者”胡琴之区别,此充分印证乐器同名却不同器之现象。“胡琴”之名在元代之前多指琵琶弹拨类乐器,如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张先所作《定西番·执胡琴者九人·般涉调》云:“捍拨紫槽金衬……三十六弦蝉闹,小弦蜂作团。听尽昭君幽怨,莫重弹。”[21]
其中所云“焊拨紫槽金衬”为琵琶的重要构造组成。白居易有诗《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新调弄谱》中“珠颗泪沾金捍拨”、贺铸《清平乐》中“船里琵琶金捍拨”即是所云捍拨。且琵琶弦数为四弦,词中所云“三十六弦蝉闹”正是为九人所演奏,此恰与词题“执胡琴者九人”相合,亦即此处“胡琴”为所咏琵琶,可见该“胡琴”不同于今日所称擦奏类弦数为二的胡琴记载。琵琶类胡琴之名甚或在清时仍有沿用,如清《笔梨园》载:“鸨儿去取了凤箫、胡琴来。媚娟接过胡琴,轻舒纤指,弹出一套《月儿高》。”[22]《月儿高》为琵琶传统文曲,明嘉靖年间《高和江东》琵琶谱手抄本对其谱即有所收。其后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成书的《弦索备考》以及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成书的《华秋苹琵琶谱》均有所录,今多流行卫仲乐的《月儿高》琵琶演奏谱。可见,同为“胡琴”之名,其实亦有不同。
7.古今同名为钲却有并非为同物者,如《续文献通考·乐考九》中有言古今两种同名钲的异实区别:“雅部有金钲……其状盖如小钟。俗部别有鼓吹钲,则形圆如铜锣……与此异。是鼓吹部之钲不应与节乐之钲同列。但元时节乐之钲,亦如铜盘,其制正与锣相似……大抵后代之钲俱不作钟式,而作锣式矣。雅部节乐之钲,其制已变。”[23]即圆如锣之鼓吹用乐钲(见图11)与同名似钟之上古语境钲(见图12)并非为同物。
8.古今名为磬亦有实之不同者。宋·王黼《宣和博古图·磬总说》有载:“《周官》则磬氏出焉。其制则中高而上大者为股;其下而小者于所当击则为鼓;上股下鼓,分为倨句之势,以成磬。”《考工记·磬氏为磬》《考工记图》《考工创物小计》等文献均对此类磬有详细所载并有图绘[24](见图13)。然而,此与唐后出现在佛教等仪式中使用的磬并非为同物(见图14)。如元代僧人德辉《敕修百丈清规》载寺中之磬,言:“磬: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直殿者鸣之。”[25]宋·陈旸《乐书·俗部·金之器》即明辨寺中之磬并言与上古石磬之所别,云:“今释氏所用铜钵亦谓之磬,盖芒名之尔。”[26]亦可为证的是今仍有传世之唐大中五年(851年)寺磬[27],《宋会要辑稿·食货》并有载此类磬在其时的铸造律令[28]。可见,上古似折尺之磬与中古似钵之磬同名但并非为同物。
9.另如对同名乐器不同用乐之考察。名为铙的乐器多出现在上古礼乐之中(见图15)。中古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铙乐器之名已趋指于似钹之铙(见图16)。在唐后大量用于释道仪式之乐,后逐渐于民间音乐中得以普遍使用,此即上古似钲之铙与中古及近古似钹之铙名实的区别。
10.今之所云大管,多指西洋木管乐器音译名“巴松”之大管(见图17)。但在清时,大管指以竹为身、芦为首哨之管(见图18)。清《清朝礼器图式·乐器》载“大管以姑冼律管为体,径二分七厘四毫,哨下口至末长五寸七分六厘”[29],并有绘图。另《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竹之属》有对大管形制尺寸、开孔位置的详细记载。
11.在古代军旅征伐生活中所使用的类似铜角之长号(见图19)与今所普遍称呼的西洋铜管乐器长号并非为一物(见图20)。如《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有载“夺获马匹、器械、长号等物”[30],以及《台湾兵备手抄》中“掌长号,擂鼓,连环对械……鸣金三声,变成光被四表阵”[31]之所载等,其余在《元史》《明史》《殊域周咨录》《清史稿》等均有载此类长号。余见图21、图22、图23、图24,兹不辄赘详举于此。
综上所述,乐器有同名异实者,即古今不同语境、不同音乐文化圈中乐器名称相同,但乐器之实并不同。正如《淮南子》所载“寒颤,惧者亦颤,此同名而异实”[32],即是所云事物具有同样的名称但却反映了不同的事实。进言之,同名异实乐器,在发音原理上有一定的共同点,这也是体现乐器同名的重要原因。但同名异实乐器同名并非为同物,在发音原理上亦有显著的区别。
以上同名异实乐器族群类属者,以及同名乐器名实所指,学界论述多有古“今”所淆,为深化乐器学在振源、策动力、振动、共鸣等声学体系族群类属研究,以上成于同名异实乐器及族群类属者,现拟发各例以表格形式胪陈于此,谨具芹献。
表1 古今同名异实乐器及其族群列属表


二、造成乐器同名异实之原因探析
析同名更要探其实,乐器二物同用一名者,必有一定的缘由。对造成乐器同名异实的原因现举案例分析如下。
(一)以乐器演奏形态者
如口琴的共同“横衔于口”,以及外来乐器输入者于当今使用的普遍性以及被大众所熟知的程度。再如古今磬器,同为击奏体鸣乐器,依声学原理和声源振动方式,同与板振动模式及特征有关。依材质看,上古磬的制作以石材质为主,故磬亦有石磬、玉磬之名,如华原石、灵璧石磬者。亦正如“磬”文字之构成,《说文》有云:“磬,乐石也。从石、殸。像悬虡之形。殳,击之也。”[33]中古之后磬,其材质以铜器为主,故亦有称铜磬。如《宋史》卷六六有载:“元丰三年八月岳州永庆寺获铜钟一、铜磬二。”[34]在共鸣上,上古“倨句一矩有半”之形似直尺磬,除声源激励与振动外,无明显共鸣系统。中古之后形似钹之磬除声源激励与振动外,有较为明显的磬体内腔气柱涡流迂回的共鸣特征。
(二)以外来乐器输入者
如洋琴,早在清阮元《两浙 轩录》卷三一有载乾隆间吴璜“洋琴行”条,其中对洋琴的来历与形制有诗咏般的解释,其云:“有客万里来大洋,携琴别调含宫商……双椎敲出声烦碎。想当风引三山高,铜弦绝点翻怒涛。彷徨龙伯罢鳌钓,珊瑚击断深夜逃。自从流移入中土,一时学习争翻谱。”[35]故今海外仍有在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世界各地流传较广的“扬琴”乐器,有德西马(Dulcimer)、欣巴罗(Cimbalom)、萨泰里(Psaltery)、海克布里(Ha-ckbrett)等名称。
轩录》卷三一有载乾隆间吴璜“洋琴行”条,其中对洋琴的来历与形制有诗咏般的解释,其云:“有客万里来大洋,携琴别调含宫商……双椎敲出声烦碎。想当风引三山高,铜弦绝点翻怒涛。彷徨龙伯罢鳌钓,珊瑚击断深夜逃。自从流移入中土,一时学习争翻谱。”[35]故今海外仍有在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世界各地流传较广的“扬琴”乐器,有德西马(Dulcimer)、欣巴罗(Cimbalom)、萨泰里(Psaltery)、海克布里(Ha-ckbrett)等名称。
“洋琴”传入中国后有流行于成都等地。如清·杨燮于嘉庆(1804年)成书发行的《锦城竹枝词》中所载:“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36]即是对成都扬琴清唱《哭五更》的描写。另如清宣统元年(1909年)刊印的《成都通览》有载逢年仍有听扬琴演奏的习俗:“正月过年,放炮、拜年……耍龙灯、耍狮子、听洋琴。”[37]
(三)以乐器结构组成与外形者
如同名为“长号”的乐器管体的可伸缩性,以及尾端同呈喇叭口状与共有的号嘴。另如古今之称腰鼓所共名在于“腰”字,今所称腰鼓,主要指挎于腰间演奏;古称腰鼓,主要体现在鼓体的广首纤腰。
(四)以气鸣乐器按键系统者
如清“朝会丹陛”之语境大管,管体中孔窍凹于管体,手指按于管体发音孔,气息激励哨簧而发音。西来“巴松”语境之大管,管体其上有凸于管体之按键系统,手指按于管体音键,气息激励哨簧而发音。
(五)以乐器振动、共鸣方式者
如古今磬器,同为击奏体鸣乐器,同与板振动模式及特征有关。依材质看,上古磬的制作以石材质为主,故磬亦有石磬、玉磬之名,如灵璧石、华原石磬者。正如“磬”以“石”部的文字构成,亦如《说文》云:“磬,乐石也。从石、殸。像悬虡之形。殳,击之也。”中古之后磬,其材质以铜器为主,故亦有名铜磬。如《宋史》所载:“元丰三年八月,岳州永庆寺获铜钟一、铜磬二。”除发声体振动外,在共鸣上,上古“倨句一矩有半”形似直尺磬无明显共鸣系统,而中古似钹之磬演奏时有磬腔气柱迂回涡流的共鸣特征。
(六)以声源策动激励者
提琴在于弓擦激励琴弦发声。古称提琴为弦间擦奏,即弓弦相交,换言之,即如《律吕正义后编·乐考十》所载“竹片为弓,马尾双弦,夹四弦间而轧之”[38]发声,亦即“以竹弓系马尾,夹于四弦间轧之”[39]。今所称提琴弓弦可分离,弓在弦外擦弦。另以振动而言,古今同名提琴之最大相异之处在于,古之语境提琴多为膜面振动,今之语境提琴为板面振动。在演奏上,古之语境提琴以坐姿演奏为主,站姿为辅。今天提琴恰以站姿演奏为主,坐姿为辅。
如同名为提琴,携同其他以弓拉弦鸣为策动力发声要素的乐器,可建立擦奏弦鸣乐器族群。余同口琴可建立簧鸣乐器族群等,以深化乐器学在振源、发声构件、振动性能、共鸣系统、调控装置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职是之故,基于对如上二十余种同名异实乐器的史源追考与辨别分析,其声学构成与同名之源有如下体现,悉陈于此:
形制尺寸、激励体系、振动体系、共鸣体系、附加装置、传导方式、按键系统(气鸣)、乐器材质、用乐类型、结构组成、演奏形态、乐器分类、外形外观、数量个体、源流传播等。
同名异实乐器在名称相同的背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声学原理与乐器族群属性联系认同。即乐器在历史不同语境中因同名而体现在发音原理上的特有关联并形成的跨族群类属,同名乐器与跨族群乐器在民族、文化、语境、边界、语音等系统地比较研究,与其在历史中古与今为何出现有乐器同名的现象,以及在乐器构造与演奏方法上所共同的体现和差异的区别,进而阐释乐器族群及其乐器学的族群认同等在历史文化语境、乐器文化内涵、乐器用乐属性等诸多相关问题,可餍之乐器研究,以促乐器学研究的不断向前开展。
注释
[1].[清]魏廷珍等:《律吕正义》卷七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708页。
[2].[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五《乐考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430页。
[3].[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九四《乐考七》,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9412页。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5页。
[5].[唐]魏徵等:《隋书·音乐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375页。
[6].[元]脱脱等:《宋史·乐志》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2993页。
[7].[元]脱脱等:《宋史·乐志》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3010页。
[8].[明]宋濂等:《元史》卷六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1701页。
[9].《大明会典》卷一八四《工部四》载:“排箫每架高一尺五寸,广一尺一寸五分,用竹十六管。”见申时行:《大明会典》,明万历内府刻本。《律吕精义》载:“大小排箫二种,皆十六管。”引自《中华大典·音律学部》,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63页。
[1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3页。
[11].[宋]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6页。
[12].[宋]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卷九二《乐》,岳麓书社,1997年,第2110页。
[13].[清]纳兰性德著,王书利主编:《纳兰性德全集》第5册,线装书局,2016年,第2007页。
[14].[唐]杜佑:《通典·乐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676页。
[1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8页。
[16].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信西古乐图》,音乐出版社,1959年。
[17].[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〇〇《乐考十三》,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9488页。
[18].[明]王圻:《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33页。
[19].赵尔巽:《清史稿》卷一〇一《乐志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2992页。
[20].赵尔巽:《清史稿》卷一〇一《乐志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3001页。
[21].邱美琼、胡建次编:《张先诗词全集》,崇文书局,2018年,第156页。
[22].[清]迷津渡者著,沂人标点:《笔梨园》,《明清稀见小说丛刊》,齐鲁书社,1996年,第800页。
[23].[清]嵇璜:《续文献通考·乐考九》卷一〇九,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66页。
[24].按:“以实物整理史料”开金石考古与文献考据之先河的朴学家程瑶田在《考工创物小计》对磬之形制尺寸在图处有更为针对性的描述与考证。(程瑶田著,陈冠明等校点:《程瑶田全集·考工创物小计》,黄山书社,2008年,第271页。)《考工记·磬氏为磬》对磬之制作方法与声音清浊之调解有详细的记载。(张青松译注:《考工记》,岳麓书社,2017年,第61页。)《考工记图》对制作磬之工匠、磬尺寸形制有细致描述,并有绘图。(戴震:《考工记图》,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5—76页。)
[25].[元]释德辉:《敕修百丈清规》卷八。亦见[元]自庆:《〈增修教苑清规〉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
[26].[宋]陈旸:《乐书·俗部·金之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
[27].刘东升主编:《中国乐器图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28].[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750页。
[29].[清]允禄、蒋溥等纂修:《清朝礼器图式·乐器》卷八,乾隆己卯年武英殿本,第74页。
[30].纪大椿、郭平梁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92页。
[31].高贤治主编:《台湾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辑,《台湾兵备手抄》,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362页。
[32].高诱:《诸子集成·淮南子语》卷一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283页。
[33].[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6年,第1368页。
[34].[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36页。
[35].[清]阮元:《两浙 轩录》,清嘉庆刻本。
轩录》,清嘉庆刻本。
[36].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739页。
[37].傅崇矩:《成都通览》,天地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38].[清]允禄等:《律吕正义后编·乐考十》,四库全书本。
[39].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第30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