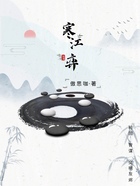
第20章 雪夜账
腊月廿三的雪片子打得户部库房的青砖地泛出冷铁色,陆九川缩在檐角斗拱后头,枣红棉袍上结满冰碴,活像只冻僵的猞猁。他往掌心哈了口白气,冻梨核在瓦片上划拉出个歪扭的“丑”字,底下当值的库兵正抱着火盆打盹,鼾声震得梁间灰鼠簌簌落灰。“老裴,你确定这库房有猫腻?”他压着嗓子朝阴影里问,回应他的是声几不可闻的银链轻响——裴照雪灰鼠裘的身影已贴在库房西窗下,鹤嘴镊正撬着窗缝里冻住的封条。
封条浆糊掺了辽东铁矿粉,在月光下泛着靛青冷光。裴照雪指尖捻开冰碴,忽见窗棂缝隙里卡着半片腌萝卜皮,盐霜下的齿痕与陆九川今早啃的那块一模一样。“陆兄倒是会留记号。”他低语间银链缠住檐角铁马,借力荡上屋顶。瓦片轻响惊醒了库兵,那人揉着眼起身的刹那,陆九川的冻梨核精准砸中火盆,爆开的炭灰迷了视线。
“走水啦!”
库兵的嚎叫撕破雪幕。裴照雪闪身翻进库房,灰鼠裘扫过满架账册,带起的风掀开本万历十九年的盐课簿——靛蓝封皮上“旧管”项的墨迹晕染出硫磺味,指尖轻搓竟簌簌落粉。陆九川从后窗滚进来,袍子后襟挂着冰溜子:“好家伙,这库房比冰窖还冷,户部的大人们查账都得揣汤婆子吧?”
两人在丈高的杉木账架间疾行,陆九川突然被地缝凸起的青砖绊了个趔趄。他骂骂咧咧抬脚要踹,却见砖缝里嵌着颗带倒刺的铁蒺藜,与鬼哭岭矿洞的暗器如出一辙。“这玩意当门槛石,比看门狗还管用!”他抠出铁蒺藜往怀里揣,袖袋里的腌菜坛子不慎滑落,酸液泼在砖面蚀出蜂窝状小孔,底下竟露出条黑黢黢的暗道。
裴照雪银链缠住陆九川腰带拽离洞口,三枚淬毒袖箭擦着袍角钉入账架。靛蓝毒烟腾起的瞬间,陆九川甩出冻梨核砸灭廊下灯笼,黑暗里传来重物坠地的闷响。他摸黑蹿向声源,枣红袍子罩住个挣扎的库吏,膝盖压住那人后颈:“兄弟,大半夜穿靛蓝短打可招灰鼠啊!”指尖触到库吏腕间硬物,竟是枚刻着“乙未”的铜钥匙。
暗道里忽传来算盘珠子的噼啪声。裴照雪燃起火折子,跃动的光影里浮现整墙铁柜,每格都标着天干地支的编号。陆九川拎着库吏的钥匙捅开“丙申七”柜门,成摞盐引如雪片倾泻,朱批日期全是腊月初七。“户部这帮孙子,做假账都懒得换个黄道吉日!”他抖开盐引对着火光,水印处隐约透出工部火器局的莲花暗纹。
裴照雪咳嗽着翻开柜底铁匣,靛蓝封皮的《四柱总录》滑落在地。书页间夹着的鱼鳞笺遇热显形,辽东银矿的走私数目与太后寿辰的用度严丝合缝。突然,陆九川拽着他扑向角落,整排铁柜被硫磺火矢射成刺猬,烈焰裹着毒烟吞噬了账册。
“走水啦!走水啦!”
真正的呼号从库外传来。裴照雪灰鼠裘卷住《四柱总录》冲出火幕,陆九川边跑边踹翻腌菜坛子,酸液浇灭追兵脚下的靛蓝引线。两人撞开北窗跃入雪地,身后库房在轰鸣中坍塌成火海,焦黑的账页残片如冥钱纷飞,落在雪地上拼出“天字十九号”的焦痕。
陆九川瘫在雪堆里喘气,从怀里摸出半块压碎的冻梨:“老裴,下回再查账,咱能挑个暖和地儿不?”裴照雪倚着枯柳展开残卷,火光映出他瞳孔中跳动的靛蓝——那并非毒发征兆,而是冰面反射的琉璃光。三丈外的冰河上,周珩的皂靴正踏着未燃尽的账页走来,鎏金鱼符勾住一片焦纸:“裴大人可知,这‘旧管’项里虚增的三千引官盐,实则是陛下修陵的椁木钱?”
周珩靴尖碾过焦黑的账页,雪地腾起硫磺味的青烟。陆九川吐出嘴里的冻梨核,核尖在冰面划出条白痕:“修陵的椁木泡盐水,您家陛下也不怕腌成腊肉?“话音未落,冰层下忽传来机括闷响,整条河面的积雪如浪翻涌,露出底下黑铁浇铸的暗仓。
裴照雪灰鼠裘扫开浮雪,银链缠住暗仓铁环。铰链绞动的轰鸣中,成排青铜箱浮出冰面,箱面阴刻的镇北侯虎头徽被硫磺蚀得斑驳。陆九川踹开最近那口箱盖,整箱带血箭头在月光下泛着靛蓝,“好家伙,这哪是修陵,是给阎王爷送聘礼吧!“
暗仓深处突然亮起火光。十二盏莲花灯沿冰河次第燃起,靛蓝灯油遇热凝成毒雾。周珩的皂靴踏过灯影,鎏金鱼符挑开某箱夹层——整摞盐引裹着辽东参须,参体刻着的微雕竟是工部火器图。裴照雪咳着翻开盐引册,指尖抚过“旧管“项虚增的三千引数目,突然将册子掷入火中。
“烧账本这招我熟!“陆九川抄起腌菜坛子泼灭火焰,酸液裹着未燃尽的纸灰凝成硬块。他掰碎灰块对着月光,焦糊的“天字十九号“水印间,隐约透出太后凤印的暗纹。冰层下传来铁链断裂声,暗仓开始缓缓下沉。
裴照雪银链卷住青铜箱甩向岸边,箱体撞碎时迸出满地黄豆——每粒豆面都刻着朝臣姓名,浸了辽东乌头汁的豆脐在雪地上滚出毒痕。陆九川捏着颗豆子嘬牙花子:“这要是炒熟了,够文武百官嚼半年舌根!“
周珩的笑声混着北风飘来:“裴大人不妨猜猜,腊月初七的宫宴菜单写着什么?“他皂靴尖踢飞盏莲花灯,灯油泼在冰面蚀出蜂窝孔洞,底下竟封着整墙琉璃柜。柜中数百个靛蓝瓷瓶浸泡着指骨,每截指骨都套着户部匠户的铜环。
陆九川抡起冻梨核砸开柜锁,酸液腐蚀处腾起刺鼻烟雾。他屏息抓出把指骨,骨缝里的铁矿砂簌簌而落:“这验尸法子新鲜,骨头渣子都能当账本使!“裴照雪突然按住他手腕,银簪尖挑开某截指骨的铜环——环内刻着的编号正是二十年前镇北侯府亲兵名录上的朱圈。
冰河对岸传来马蹄疾响。太后仪仗的鎏金顶盖刺破雪幕,八抬暖轿里飘出句:“裴卿,哀家这出戏可还入眼?“轿帘掀开的刹那,陆九川的腌菜坛子脱手飞出,酸液泼在轿夫皂靴上蚀出靛蓝毒纹——与裴照雪腕间的如出一辙。
裴照雪咳出黑血,染得雪地像打翻砚台。他抖开灰鼠裘残片,补丁缺口处的鱼符拓片正嵌进琉璃柜某处凹槽。柜体轰然中开,露出整墙的《四柱密档》,每册封面都粘着片腌萝卜皮——正是陆九川这些天沿途留下的记号。
“这萝卜要是会说话,早该封个五品掌印!“陆九川踹翻琉璃柜,密档如雪崩倾泻。太后腕间的鎏金镯突然射向裴照雪心口,被他用冻梨核凌空击落。酸液腐蚀镯面露出夹层,半枚带血的虎头符正与灰鼠裘补丁纹样吻合。
冰面崩裂的巨响中,暗仓彻底沉入河底。周珩立在浮冰上,皂靴碾碎最后几粒毒豆:“裴大人现在可知,这四柱账目里真正要藏的,是陛下永生的秘密?“他甩袖时震落满襟雪粒,每颗雪粒都裹着辽东银矿的硫磺结晶,遇水即燃成靛蓝鬼火。
五更梆子敲破黎明时,裴照雪瘫坐在残账堆里。腕间毒纹消退处泛起冰晶,瞳孔中的靛蓝光泽却愈发明亮。陆九川嚼着不知从哪摸出的酱瓜,冻梨核往冰面一敲:“这烂账要是清不完,咱去御膳房偷两坛好酒,醉死算球!“
晨光刺破云层那刻,整条冰河腾起硫磺火焰。燃烧的账页灰烬在空中拼出“腊月初七“的字样,纷纷扬扬落在太后的凤辇顶盖上,像场迟了二十年的丧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