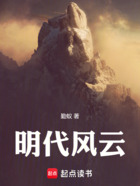
第77章 宣化城头那阵寒风
就在景泰帝正欲挥动京察之剑整饬吏治,追缴赃款以解国库空虚之时,京南官道上,奔赴治水的团营精锐正在晨雾中疾行。
他们沉重的脚步声震得道旁枯草上的露珠簌簌坠落。
为首的参将王获骑着一匹枣红马行在队伍最前,不时回头催促:“快些!再快些!”
可这些精锐步卒即便全力赶路,一日也不过行进五十余里。
队伍后部,二百余名锦衣卫缇骑显得格外醒目。
他们身着暗红色袍服,腰间绣春刀随着马背起伏而轻轻晃动。
本该疾驰如风的缇骑此刻却不得不压着马速——沿途驿站马匹不足,商辂大人严令他们必须随大军同行。
“谢哥!”一个年轻缇骑突然压低声音呼唤,他面容青涩,约莫二十余岁。
前方马背上的谢冬闻声勒马,他调转马头时,腰间铜牌在晨光中闪过一道金光。
“陈福生?”他皱眉道,“何事这么鬼祟?”
陈福生轻夹马腹,战马不由得向前蹿出几步。
他贴近谢冬身侧,声音压得极低:“谢哥,门佥事那日密令……”
话到此处突然一顿,他警惕地扫视四周,确认最近的兵卒都在十步开外,这才继续道:
“那桩差事,终究还是落在你我肩上了。”
“商大人这次……”谢冬咬着下唇,声音里混着马蹄踏碎枯枝的脆响,“当真是慧眼如炬啊。”
忽又话锋一转,嘴角扯出个古怪的笑:“不过太子殿下此刻已然不在,倒让咱们能偷得几日清闲。”
原来日前商辂亲自挑选的二百缇骑中,竟阴差阳错混进了他们这两个门达安插的暗桩。
更讽刺的是,他们肩负的竟是刺杀太子的泼天大事。
“可到了张秋呢……”
陈福生将手中缰绳收了收,胯下战马不安地打了个响鼻。
他年轻的面庞在晨光中显得有些苍白,“咱们可就再没推脱的余地了。”
谢冬的目光陡然锐利起来。
他忽然伸手按住陈福生的肩膀,力道大得惊人:“慎言!”
随即又压低声音:“你当门佥事为何每月都遣人给咱们家中送米送面?”
谢冬闻言,握着缰绳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他比陈福生年长五岁,眼角已有了些许细纹,此刻在晨光中更显沧桑。
“福生啊……”
他声音沙哑,喉结滚动了几下,“你还年轻,孤身一人无牵无挂。”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块褪色的绣帕,上面歪歪扭扭绣着个“安”字,“可我家里……还有个刚会叫爹的小崽子……”
陈福生的手猛地一颤,缰绳在掌心勒出红痕。
“我爹的腿疾……”他声音发紧,似乎在回忆,“还有十五岁的小弟……”
他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惧色,“太子身边那些侍卫,哪个不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咱们怕是连衣角都碰不着,就要步那钱勇的后尘!”
谢冬突然也勒住马,战马不安地踏着步子。
他直视着陈福生的眼睛,目光如刀。
“兄弟……”他声音压得极低,几乎淹没在晨风里,“哥哥有几句话……”
“你若不想听,现在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陈福生一把拽住谢冬:“咱们多年生死兄弟,过命的交情,有什么不能直说?”
谢冬环顾四周,压低声音:“门佥事整日把'正统血脉'挂在嘴边,还说什么事成之后保咱们一个千户的职位……”
他冷笑一声,“可咱们这样的小卒子,龙椅上坐的是太上皇还是当今陛下,与我们何干?
每月不就领那些粮饷!
再说咱们这差事,成了是灭口,败了是替罪羊!
门达早给咱们备好了棺材!加官进爵有何用?”
原来门达在训练死士时,不仅扣着他们的家眷作质,更日复一日地灌输所谓“忠义之道”,那些刻意安排的恩惠,都是为了把这群棋子打磨得更加趁手。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无人靠近,便继续说道:“昨日六百里加急送到时,我亲眼见太子那焦躁不安的神情,不似门达说的那般不堪。”
陈福生闻言,目光闪烁。
“太子甚至连夜驰骋张秋去了,这决计装不出来的,”他抬眼望向前方蜿蜒曲折的队伍,“这会儿怕是已到济南府了吧?”
“不如……”
谢冬策马靠近陈福生,低声继续说道,“咱们就推说近不得身!”
“可门大人给的期限,”陈福生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月底若无消息,你我家小恐怕……”
一阵初春的凉风卷着沙砾刮过,两人同时打了个寒颤——这恐怕又是一个死局啊!
-----------------
这阵凉风同样卷过宣化城头,镇朔将军印在张倪腰间沉甸甸地坠着。
兵部武选司主事李文昌落后半步,目光扫过城楼下灰蒙蒙的校场。
远处八路分守的烟墩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列沉默的哨兵。
“张总兵,按规制,到任三日内须点验军籍、清核防务。”
李文昌的声音裹在风里,带着几分文官的审慎。
张倪未答,掌心轻轻抚摸着城砖上刀刻般的裂痕——这是瓦刺骑兵掠城时留下的。
他转身望向城楼下的队列,分守中路参将赵延林、北路参将王洪卫、东路参将李贤超等各路尽数到齐,他们甲胄未卸,铁盔下的面容如刀削般冷峻,腰间雁翎刀鞘上凝着白霜,刀柄缠着的牛皮绳已被血渍浸得发黑。
一侧的游击将军马严壮、符逸飞各领着三百标兵按刀而立。
马严壮座下那匹大青马焦躁地刨着冻土,鼻息喷出的白雾里混着血腥气——昨夜他们刚巡边归来。
“擂鼓。”张倪开口,声如铁砧。
三通鼓毕,屯田军、营兵、卫所残卒从四面堡寨聚来,像一条条瘦长的影子匍匐在地上。
李文昌展开黄册,“原额官军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的字迹映入他的眼帘——这是宣德年间的数字。
粗略一看,如今名册上朱笔勾销的逃兵缺额,竟接近四成。
他不禁为这位头一回真正执掌兵符的将军多了几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