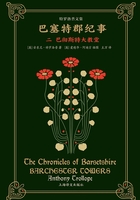
第1章 谁将成为新主教?
一八五一年七月的下半个月,大教堂镇巴彻斯特的居民一连十天无时无刻不在打听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作出各各不同的答复:谁将成为新主教?
先前有好多年,老格伦雷博士[1]一直谦和恭谨地担任着这个圣职。他的逝世恰恰发生在某勋爵的内阁就要由另一位勋爵的内阁取代的时候[2]。那位善良的老人病了不少日子,拖延了许久。后来,在那些有关的人看来,这成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新的任命将由一个保守党政府来作出呢,还是由一个自由党政府来作出?
大伙儿都知道得很清楚,即将离任的首相已经挑好了人选,要是这个问题由他来定,那么主教冠就会戴到老主教的儿子格伦雷会吏长[3]的头上。会吏长早就在处理主教区的事务了。在他父亲下世之前好几个月,人们就已经十拿九稳地传说,他会继承下他父亲的这份荣耀。
格伦雷主教是平静地、慢悠悠地死去的,既没有痛苦,也并不激动,就和他活着时的情况一样。气息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从他喉咙里微弱下去,因此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是死是活早就成为疑问了。
那阵儿对会吏长说来,的确是难熬的日子,当时有权任命主教的那些人是打算让他接下他父亲的圣职的。不过请不要认为我是说,首相曾经讲过一些话答应把主教职位授给格伦雷博士。他为人老谋深算,决不会这么做的。有一句关于葬送了猫的性命的谚语[4]。凡是对于政府大小官职略知一二的人,全都十分清楚,诺言不必用明确的语言也可以作出,尽管大人物也许只小声说了一句,“某某先生的确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仰仗他鼻息的人就可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这样一句话倒是私下说过了,听见的人全都知道,这是表示巴彻斯特主教区的事务不应从会吏长的手里夺走。当时的那位首相在牛津深受爱戴,新近还在拉撒路[5]学院院长的宅子里度过了一夜。话说拉撒路学院的院长——顺带提一提,拉撒路学院从多方面看来,都是牛津最阔绰、最愉快的学院,——是会吏长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信赖的顾问。首相光临的时候,格伦雷博士当然也在场,这次会面很亲切。第二天早晨,院长格温博士告诉会吏长,在他看来,这件事算是定了。
这时候,主教生命垂危,可是内阁也风雨飘摇。格伦雷博士由牛津回来,满心欢喜、兴高采烈。他在主教公馆里重新担起了他的职责,继续对父亲履行做儿子应尽的最后一些孝道。替他说句公道话,这一点他倒是体贴而关切地做了。他平时为人多少有点儿世故,这份体贴关切实在是别人没有料到的。
一个月以前,内科大夫们都说,这个垂危的老人至多只能拖延四星期的时间。一个月过去了,大夫们全很惊异,于是又说至多还能活两星期。老头儿单靠喝酒维持生命,但是两星期过去后,他还活着,内阁倒台的消息变得更加频繁了。伦敦的两位名医兰姆达·缪纽爵士和奥米克龙·派伊爵士,第五次又跑来,摆动着挺有学问的脑袋诊断说,再活一星期是不可能的了。当他们在主教公馆的饭厅里坐下吃午饭时,他们把自己私下听到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会吏长:内阁在五天之内准会倒台。儿子回到父亲的房间里去,亲手把维持生命的少量马德拉酒[6]给父亲喝了,然后在床旁坐下,估摸着自己的机会。
内阁在五天之内就要垮台,他爸爸在几天之内就要去世呢——不啊,他把对这问题的这种想法排开。内阁就要垮台,主教区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就要空了出来。接下去出来执政的是哪些人,这是拿不大准的,而且组成一个内阁总得花去一个星期。出缺的职位会不会由离任的人在那一星期内委派好呢?格伦雷博士认为事情大概会是这样,不过他了解得并不清楚。接着,他又对自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多么无知感到惊讶。
他极力想把心思从这个问题上排开,可是他办不到。这场赛跑这么接近,赌注又这么大。他随即望望垂死的人那张毫无表情的、平静的脸。脸上并没有死亡或患病的迹象,它只是比早先消瘦了点儿,稍许苍白了点儿,老年人的皱纹更为明显了点儿,不过据他看来,也许还可以弥留好几星期。兰姆达·缪纽爵士和奥米克龙·派伊爵士的诊断已经错了三次,还可能再错上三次。老主教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昏昏沉沉地睡上二十小时,在他清醒的短暂时刻里,他认得出他的儿子和亲爱的老友,会吏长的岳父哈定先生,并且总为他们的关怀爱护亲切地道谢。这时候,他躺在床上,安安逸逸,像个婴儿似的睡着,嘴微微张着,几丝灰白的头发从睡帽下面乱蓬蓬地支了出来,他的呼吸是没有声息的,一只瘦削、苍白的手搁在床罩上,一动也不动。没有什么事会比这位老人从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更轻松的了。
可是坐在一旁守着的人的情绪,却压根儿并不轻松。他知道要么就是眼下,要么就永远不会实现了。他已经五十出头,这会儿即将离任的朋友们不大可能会很快就官复原职。除了现在在职、马上就要下台的那个人,大概没有一位英国首相会想着委派格伦雷博士当一位主教。这样,他默然而伤心地深思了许久,然后又凝视着那张还有生气的脸,终于斗胆询问自己,他是否当真渴望他爸爸死呢。
这一番着力倒是大有裨益的,那句话马上便得到了答复。这个高傲、世故、利欲熏心的人在床旁双膝跪倒,握着主教的一只手,热切地祈祷,恳求自己的罪恶可以得到宽恕。
他的脸还埋在衣服里的时候,卧房房门悄没声地打开了,哈定先生轻手轻脚走了进来。哈定先生几乎和会吏长一样,经常到那个床旁边来,所以他的进进出出也和他女婿一样,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会吏长还没有看到他,他已经紧紧站到了女婿的身旁,要不是因为担心会突然引起一阵惊慌,影响到垂死的人,那么他也会跪下祈祷的。但是,格伦雷博士立刻瞥见了他,连忙站起身。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哈定先生握着他的两手,热诚地紧捏了一下。那当儿,他们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密,而后来出现的情况竟然把这种情绪很好地保存下去。他们彼此紧握着手站在那儿时,泪水扑扑簌簌地淌下了两人的面颊。
“上帝保佑你们,亲爱的,”——主教清醒过来,用虚弱的声音说,“——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俩,亲爱的孩子和教友。”说完,他便死了。
他嗓子里并没有很响的格格声,也没有令人惊骇的挣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死亡迹象,不过下巴颏儿比平日稍微耷拉下点儿,原先经常阖上昏睡的眼睛,这时候却呆滞地睁着。哈定先生和格伦雷博士当时全不知道他已经去了,尽管两人都有点儿疑心。
“我想他已经去啦,”哈定先生说,仍旧紧握着另一个人的双手,“我想——不啊,我希望他是如此[7]。”
“我来打一下铃,”另一个几乎是悄没声地说,“菲利普斯太太应该待在这儿的。”
护士菲利普斯太太不一会儿便走进房来,用熟练的手立即把那双直瞪瞪的眼睛阖上了。
“他已经去了吗,菲利普斯太太?”哈定先生问。
“主教大人不在啦,”菲利普斯太太说,同时回过身,神情庄重地行了一个屈膝礼[8],“我可从没有见到过有谁和大人一样,像个酣睡的婴孩似的就走了。”
“这是个很大的解脱,会吏长,”哈定先生说,“是个很大的解脱——亲爱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啊,但愿咱们临终的时刻也像他一样平静安宁!”
“当然啰,”菲利普斯太太说,“感谢上帝,他那么慈悲,不过就一位温和宽厚、谈吐高雅的基督徒来讲,大人是——”菲利普斯太太带着真挚的、自发的悲伤心情,用雪白的围裙遮住了她的眨动的眼睛。
“他这样去了,你不能不感到欣慰。”哈定先生说,他还在安慰他的女婿。然而那会儿,会吏长的心思已经从他父亲刚死的这间房转到首相的私人办公室去了。他方才曾经尽力为父亲的生命祈祷,可是既然他已经去世,时光太宝贵,决不能再失去了。如今,在主教逝世这件事上延误时间是无益的——为了装出一种无聊的情绪而可能丧失一切,这也是无益的。
但是岳父站在那儿握住他的手,他该怎样举措呢?他该怎样不显得毫无父子之情,忘却主教——忽略掉他已经失去的,单想到他可能会获得的呢?
“是呀,敢情是这样,”他最后这么说了一句来回答哈定先生,“这件事咱们大伙儿早就料到啦。”
哈定先生挽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出了那间房。“明儿早晨咱们会再见到他的,”他说,“这会儿最好让女人们去照料吧。”这样,他们走下楼去。
那时已经是傍晚,天快黑下来了。当天晚上就应该让首相知道这个主教区空出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这一点,因此在回答哈定先生进一步的安慰时,会吏长提议应该立刻打一份电报到伦敦去。哈定先生先前发现格伦雷博士像他以为的那样,十分激动,当真感到有点儿惊讶;听到这话,的确吃了一惊,不过他并没有表示反对。他知道会吏长颇有希望接下他父亲的职位,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希望已经变得多么大。
“是呀,”格伦雷博士定住神,摆脱了自己的软弱说,“咱们一定要立刻发一份电报去。咱们不知道拖延会造成什么后果。您可以去办一办吗?”
“我!是啊,当然可以。我什么事都乐意办,只是我不知道你想要办的到底是什么事。”
格伦雷博士在写字台面前坐下,拿过钢笔墨水,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下面这样几句:
致电
唐宁街(或其他地方)××伯爵:
“巴彻斯特主教病故。”
塞浦蒂麦斯·哈定牧师谨呈。
“喏,”他说,“把这拿到火车站旁边的电报局去,照原样发出。他们可能要请您把电文抄在他们的一张纸条上。您要办的就是这件事。接下去您还得付给他们半克朗[9]。”会吏长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需要的钱来。
哈定先生觉得自己活脱就像一个小听差,还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不合适的时候奉命去办理这些事务,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就接下那张纸条和交出来的钱。
“可是你在上面署了我的姓名,会吏长。”
“是的,”另一个说,“得有人家知道的一位牧师署名。有谁的名字比您这样一位老朋友的更合适呢?伯爵不会看名字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不过,亲爱的哈定先生,请您务必不要耽搁时间吧。”
哈定先生在去车站的路上刚走到书房门口,突然想起自己刚才走进可怜的主教的卧房时带来的那条新闻。当时,他发觉谈论世俗的消息太不合时宜,因此把到了嘴边的话强忍住了。紧接着出现的场面把那件事一时排开,使他完全忘了。
“可是,会吏长,”他转回来说,“我忘了告诉你——内阁已经下台啦。”
“下台啦!”会吏长突然喊起来,那种腔调把他的焦急沮丧心情表达得明白无误,虽然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竭力想约束住自己。“下台啦!谁告诉您的?”
哈定先生解释说,这条新闻是通过电报传来,由贾德威克先生带到主教公馆门口的。
会吏长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沉思着。哈定先生站在一旁望着他。“没关系,”会吏长最后说,“仍旧把电报发出去。这消息非得送给一个人。眼下,没有别人可以收下它。立刻就发,亲爱的爸爸。您知道,我要是可以亲自去发,就不会麻烦您啦。几分钟的时间都非常重要。”
哈定先生走出去,把电报发了。我们不妨跟着电报去到它的目的地。在它由巴彻斯特发出后三十分钟,它就给送进××伯爵的内书房,交到了他的手里。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待在那儿可能不得不拟定一些多么精心构思的信件,多么雄辩有力的呼吁,多么义愤填膺的疏谏,这是可以想象而难以叙述的!他像一位英国贵族那样站在那儿,背对着炉火,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怎样在为他的占了上风的对手们准备即将发出的霹雳啊,——他的敏锐的目光里怎样闪射出怒火,额头上怎样焕发着爱国的热忱,——他想到他的心情沉重的同僚们,又怎样地在跺他的脚啊,——他想到他们中有一位过去多么精明时,几乎咒骂出声来,——这一切我的富有想象力的读者都可以想象得出。但是,他是这么忙着吗?没有,历史与实情迫使我来加以否认。他当时正安安逸逸地靠在一张躺椅上,研究着一份纽马克特[10]的名单。在桌上他的胳膊肘儿旁边,摊开放着一部他在阅读的、毛边的法国小说。
他把盛着那份电报的封套拆开,看完以后,拿起钢笔在背面写道:
致××伯爵,
××伯爵致意。
随后,他又把电报转出去了。
这样,便断送了我们倒霉的朋友享有一位主教的种种荣耀的机会。
报上举出了好多位牧师的姓名,认为是巴彻斯特主教的人选。《英国老祖母》为了向上一届内阁致意,说格温博士是适当的人选。这对格伦雷博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却注定不会看到自己由他的朋友来取代。《国教信徒》满有把握地主张,应当任命伦敦的一位严于律己的主要传道士。而一份据信知道不少官方内情的晚报《东半球》,则赞成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一位精通岩石与矿物、但许多人全认为对宗教问题不持有任何特殊教义的先生。我们全都知道,那份日报《朱庇特》[11]才是各种确凿可靠的消息唯一真正的来源,它有好几天都保持缄默,后来终于发表意见了。所有那几个候选人的长处它全都议论到,并且相当不礼貌地一个个排除掉了。接下去,《朱庇特》宣布,普劳迪博士才是胜任的人。
普劳迪博士正是内定的人选。在前主教去世后仅仅一个月,普劳迪博士便吻了女王的手[12],成为选定的继任人。
我们非得请求读者允许,在会吏长满心忧伤,坐在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13]牧师公馆的书房里时,拉下一幅帷幔,把他的种种伤心遮盖起来。在那份电报发出后的一天,他听说××伯爵同意着手组阁了。从那时刻起,他就知道自己接任主教的机会全完了。许多人都会认为,他为失去主教大权而伤心失望是恶劣的,垂涎那种权力也是恶劣的,而且就连那样想到它,在那时刻想到它,都是恶劣的。
对于这些指责,我不能说我完全同意。虽然nolo episcopari[14]这句话还在使用,可是它跟人类种种愿望的趋向大相径庭,因此不能认为是表达了英国国教崭露头角的教士们的真正抱负。一位律师谋求当上一名法官,或者使用各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他的愿望,这并不算犯罪。一个年轻的外交官指望当上一个第一流使馆的使节时,也抱有相当大的雄心壮志。一个贫穷的小说家试图和狄更斯一争高低,或者试图胜过菲茨杰姆斯[15],并没有因此就犯下过错,尽管他可能是愚蠢的。西德尼·史密斯[16]说,在那些不讲信义的日子里,我们不能指望看到堂堂正正的圣保罗[17]不屑当一个副牧师,这话可一点儿不错。如果我们指望我们的教士超乎一般人,那么我们大概得教导自己去思索,他们实在还不及一般人,所以不容牧师有一般人的抱负,希望借此来提高他们的声望,这是不大现实的。
我们的会吏长是热中于名利的——我们当中有谁不是这样呢?他雄心勃勃——我们当中有谁感到羞愧,不肯承认具有“思想高超的人的最大弱点”[18]呢?读者们会说,他是贪财好利的。不啊——他想当巴彻斯特主教倒并不是因为他爱钱财。他是他爸爸的独子,爸爸给他留下了大宗的钱财。他的圣职每年使他可以收入将近三千镑。而根据国教教务委员会[19]所削减的,主教也只有五千镑。他当会吏长比当主教更会成为一个阔人。不过他当然渴望独当一面,他的确渴望当上主教,置身在王国的上院议员们之中[20];如果非把实情全说出来不可的话,他的确渴望他的同道教友们都管他称作“大人”。
然而,不问他的希望是罪恶的还是无罪的,它们却注定不能实现。普劳迪博士就任了巴彻斯特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