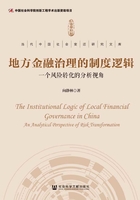
在传统中发展现代
静林寄来书稿《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嘱我写序,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请老师写序时的情景。当年,我拿着书稿请老师写序,老师秒应。对静林的托付,我自然没有迟疑。老师们总以为在学生的成长中自己有一份责任,支持学生成长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大概是中国的师生之道吧。
老师们都知道,大学是通行于世的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还是中国现代化痛苦进程的产物。在现代教育制度中,老师教书只是一份职业,学生是否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与老师无关;学生是否毕业,则是学校的事情,也与老师无关;老师的职责是教好书、做好科研。课程一旦教完,师生之间的关系便告结束;学生毕业走出校门,更与老师无关了。
如果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在零基础上建立的,估计,对上面的角色划分没有异议,师生关系也应该是制度约定的样子。可事实是,在采用现代教育制度之前,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师生关系史,早已形成了一套师生之间的行动规则。“教不严,师之惰”,“师生如父子”等等,让老师对学生的许多责任与生俱来;反过来,学生对老师的特别尊敬也理所当然,师生关系俨然是中国社会秩序中最具有示范性的一部分。尽管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推行了一个多世纪,可静林嘱我写序和我的承诺,一如我请老师写序和老师的应允,我们似乎依然在践行中国古老的师生之道,而不是遵循现代教育制度的岗位职责。同时我还相信,在我身上体现的师生之道在中国现代教育实践中绝不是个案!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了一百多年,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传统社会规则[1](social norms)并没有因为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等的发展而完全代之以现代规则(rule by law)。许多传统社会规则就像师生之道一样,依然在维系着中国社会的延续,凝聚着社会的纽带,塑造着社会的秩序。社会规则无处不在,新生事物的发展,大抵总离不开社会规则尤其是传统社会的约束,这大概是戴维斯特别区分成文规则和行动规则的应有之义;[2]对中国社会的广泛调研也让我观察到,越是地方社会,地方性知识[3]的生命力越顽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越大。
《地方金融治理的制度逻辑》探讨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东南的越融市,私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依照现代市场制度逻辑,这是市场的事儿。如果发生挤兑或金融闭环的任何一类行动者“跑路”而使闭环断裂进而给利益相关方带来风险或损失,均可以依照市场规则和法治路径(rule of law)寻求问题的解决,给各方一个说法,与地方政府和社会无关(irrelevant)。可事实并非按照市场制度的理想逻辑在发展,而是在传统社会逻辑与现代市场逻辑之间摇摆。在风险发生之后,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利益相关方除了寻求法律途径依法办事,在法制失效的情境下,也会运用地方性社会规则进行应对,包括围堵政府,引发甚至制造局部性社会失序或动荡。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教训清单中,社会动荡是每个行动者都会遭受损失的社会场景;在共识的社会逻辑中,社会动荡是底线。触及这个底线的事务便不再只是地方的事务,而是牵涉整体的社会事务,不仅受到地方社会规则的约束,更受到整体社会规则的约束。对越融市而言,在民间金融不断触发社会风险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试图创新金融治理实践,不仅是预防发生社会动荡的地方性努力,也是上级政府甚至整体社会的要求和期待。在现代与传统金融规则的交互作用中,方式之一是建立有政府背书的地方金融活动制度与机构(越融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用现代金融制度和机制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防患于未然,把金融风险触发社会风险的苗头扼杀于源头。
政府的设想是,借服务中心的壳把传统民间金融活动中的利益纠葛引向现代市场治理。在这个进程中,政府的职责是为服务中心植入现代市场规则和治理机制,让服务中心依法依规有序运营。有意思的是,事实再一次回到了戴维斯悖论,理想与事实之间总是存在无法填满的距离。用流行的俗语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政府原本设想着,一旦植入进程结束,便可以全身退出服务中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事物发展演化却是,即使植入进程已经完满结束,政府不仅难以退出服务中心,甚至还卷入得更深,被迫介入具体纠纷的处置之中,让看起来纯粹是市场的事儿,至多也只是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事务变成了“市场—社会—政府”之间的三角闭环互动,把一个地方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都卷入到金融活动的调解与处置之中。政府不仅要和事,还要扮演“兜底者”的角色。其实,“政府兜底”现象不仅出现在越融市对金融活动的治理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许多涉及社会的事务处置中,“政府兜底”现象非常普遍。[4]
在对越融市的实地调查中,静林敏锐地觉察到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地方金融治理的实践问题,更是从地方金融治理出发,以小见大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这一敏感,则触及了一些理论的前沿。
过去的40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次探索,是从计划经济、单位制、城乡分割体制向市场经济、国民社会、城乡融合体制发展的探索。在这项历史性的、规模最大的人类社会探索中,社会科学家们也进行了广泛的努力。在社会学探讨中的“国家与社会”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政府与市场”是通行于西方世界的基本理论框架,在面对如此重大的中国社会变迁中,这两个框架成了两把万能钥匙,不断被应用于对中国现象的分析,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性的质疑;由这两个分析框架产生的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可是,正如静林在对文献的回顾中指出的,学者们忽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背后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市场主体的反向作用对政府角色和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对政府与市场主体互动的过程机制分析;较少明确地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纳入社会情景中进行考察;较少关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等,不一而足。
的确,在越融市金融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发现,社会学对服务中心的分析无法简单地抛开市场尤其是市场化进程来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一如格兰诺维特(2019)讨论的,即使把金融活动放在社会中,也无法忽视社会规则尤其是地方性社会规则的影响来探讨政府与市场,“政府—市场—社会”在服务中心的运营中天然地纠缠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闭环。[5]在既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都从收益分配入手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征与互动机制,静林则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切入点:风险转化。如果说威廉姆森(2016)在探讨组织治理中成功地植入了交易成本变量,让组织治理几乎成为统摄相关讨论的总框架;[6]那么,我认为风险转化视角似乎具有相似的潜力。
只是,挖掘其中的潜力需要基于以下几个基础。
第一,把“风险转化”置于“政府—市场—社会”的闭环互动中。任何一方对风险的规避其实都以其他两方行动者的合作为前提,这是社会事实,不只是思想实验。在地方社会发展中,我们曾尝试以三方行动逻辑的组合模式为话题,探讨了三种类型的闭环互动,其中三方合作的闭环互动可以带来社会福利最优。[7]静林和我们的探讨都说明,三方闭环互动不仅是地方性的,在一个急剧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它也是整体性的。对一个整体性社会现象的探讨,如果忽视社会事实,至多只能获得思想实验的愉悦,而无法通过贡献真知灼见来促进对社会对理解。
第二,把闭环互动放在互动发生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中。无论是我们曾经讨论的闭环互动,还是在静林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互动发生的具体社会中,地方性社会规则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直接与现代法治产生交互。大量事实表明,在一个有着深厚社会传统的社会,制度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换频道,混合治理可能是一个阶段,也可能是一个“新常态”。其实,社会规则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已经很好地预示了市场规则、政府规则、社会规则之间必须妥协,否则,社会动荡是哪一方都无法承受的风险之重。静林探讨的越融市金融治理逻辑是这个大逻辑最好的例证,其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把地方社会的上位规则即整体性政府规则的影响纳入其中进行分析。
作为一个极好的也是前沿的起点,我相信静林未来可努力的空间不可谓不大。其中,把社会规则作为理解人类在传统基础上发展现代的线索,或许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邱泽奇
2019年5月于皂君庙
[1] Sherif,M.,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NewYork:Harper,1936);Lapinski,M.K.,Rimal,R.N.,“An 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15(2005):127-147.
[2] Davis,Kingsley,Human Society(Oxford,England:The Macmillan Co.,1949).
[3]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 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韩志明:《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李婷婷,《“兜底”的调解者:转型期中国冲突管理的迷局与逻辑》,《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杨华:《“政府兜底”: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的现象与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2期。
[5] 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6] 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石烁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7] 邱泽奇、邵敬:《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格局:三秩并行——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第5期;邱泽奇:《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第1期;邱泽奇、李澄一:《三秩归一与秩序分化——新产业触发乡村秩序变迁的逻辑》,《社会学评论》201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