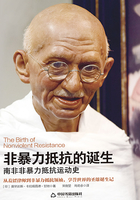
2.在德兰士瓦从业
我很快提出在德兰士瓦从业的申请。(P.134)有人担心当地法律界可能也会反对,结果证明这种担忧毫无根据。我在最高法院注册律师,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事务所。在德兰士瓦,就数约翰内斯堡市的印度人最多,所以从公益事业和自谋生计的角度而言,这儿最适合我安顿下来。亚裔人管理局的腐败程度让我每天都大长见识,这也是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协会努力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把撤销1885年的《第三法案》作为长期目标放到了次要地位。当前的目标仅限于如何面对来势汹汹的亚裔人管理局,谋求自保。印度侨民代表团谒见了多位英国政要,包括出访德兰士瓦的米尔纳勋爵和塞尔伯恩勋爵,德兰士瓦省副总督亚瑟·罗雷爵士(后来他出任马德拉斯总督) ,以及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我经常去拜见政府官员。零零散散地,我们解决了一点问题,但都只是东拼西凑。我们得到的慰藉少得可怜,就像被强盗洗劫一空的人,哀求了半天也只讨回一点廉价的财物。(P.135)前面我提到过亚裔人管理局那两名被开除的官员,就是我们强烈抗议的成果。事实证明,我们对政府要限制印度移民的担忧不无道理。欧洲移民不再需要通行证,但印度人不行。之前布尔政府虽有严苛的反亚洲人立法,但从未严格执行。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而是因为行政的松懈。英国官员可没那么好混日子。英国宪法历史悠久,中规中矩,官员必须像机器一样依法办事。有一整套逐级审查体系限制官员做事的自由度。因此,在大英宪政体系中,如果政府政策开明,官员待臣民就极为宽松。反之,如果政策严苛压抑,官员对臣民就手段强硬。而之前的布尔共和国,情况正好相反:臣民能否从开明的法律充分获益完全取决于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就这样,大英帝国在德兰士瓦确立政权后,所有不利于印度人的法律执行得越来越严格。(P.136)原有的空子全都被仔细地堵上了。前面已经看到,亚裔人管理局的运作肯定会苛刻行事。因此,撤销原来的法律毫无可能。印度人能做的只有试探,看看这些严厉的官员在办事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松动。
,以及其他职位较低的官员。我经常去拜见政府官员。零零散散地,我们解决了一点问题,但都只是东拼西凑。我们得到的慰藉少得可怜,就像被强盗洗劫一空的人,哀求了半天也只讨回一点廉价的财物。(P.135)前面我提到过亚裔人管理局那两名被开除的官员,就是我们强烈抗议的成果。事实证明,我们对政府要限制印度移民的担忧不无道理。欧洲移民不再需要通行证,但印度人不行。之前布尔政府虽有严苛的反亚洲人立法,但从未严格执行。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而是因为行政的松懈。英国官员可没那么好混日子。英国宪法历史悠久,中规中矩,官员必须像机器一样依法办事。有一整套逐级审查体系限制官员做事的自由度。因此,在大英宪政体系中,如果政府政策开明,官员待臣民就极为宽松。反之,如果政策严苛压抑,官员对臣民就手段强硬。而之前的布尔共和国,情况正好相反:臣民能否从开明的法律充分获益完全取决于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就这样,大英帝国在德兰士瓦确立政权后,所有不利于印度人的法律执行得越来越严格。(P.136)原有的空子全都被仔细地堵上了。前面已经看到,亚裔人管理局的运作肯定会苛刻行事。因此,撤销原来的法律毫无可能。印度人能做的只有试探,看看这些严厉的官员在办事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松动。
有一个原则问题需在此事先探讨一下,以便大家更好理解印度侨民的想法,以及后面情况的发展。大英帝国在德兰士瓦和自由邦确立管制之后,米尔纳勋爵就委派一个委员会整理清单,列出原先这两个布尔共和国限制臣民自由,或违背英国宪法的法律法规。原先那些反印度人法规无疑应被纳入其中。可是米尔纳勋爵这么做,并不是为给印度侨民平怨,而是要让英国侨民息怒。他想在第一时间就废除那些压制英国人的旧法。委员会很快就递交了报告,勋爵大人大笔一挥,原先大大小小不利于英国人的法令即告作废。(P.137)
这个委员会也准备了一份反印度人的法规清单。清单以书的形式出版,却被亚裔人管理局轻易拿来当作工作手册。而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滥用。
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对印度人点名道姓,但行政人员可以在执行时酌情处理,就算不上有意针对印度人,而是适用于全体子民的普通法;作为普通法,这些法律法规做出的是整体性规定,只是行政人员在执法时对印度人特别严格,原本也能达到立法者针对印度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在执行过程中,谁也不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随着时间淡化掉原来的怨恨,政府也就没必要修改法律,只要执法较为开明,就足以化解愤愤不平的印度人。这样的法律,我称之为普通法,而与之相反的则名为特殊法,或种族法。后一种即所谓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法律”(colourbar),也就是仅凭肤色判断,强加于欧洲人除外的黑人或黄种人的法律。
让我从已实施的法律中举例说明。读者们应当还记得,(P.138)纳塔尔地区曾颁布首部《剥夺选举权法案》,但其因取消亚裔选民的资格,后未获大英帝国政府通过。现在,政府若能修订反印度人之法,极大教化民意,则大多数民众不仅不会仇视亚裔人,反而会生出友善之心。民众和睦,自会消除原先法律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刚才提及的《剥夺选举权法案》就是种族歧视、阶层歧视立法的一个例证。政府废除了这部法案,颁布新法,取而代之。两者实际上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但后者剔除了种族区分的话语,更具普遍性。其中一款条文内容如下:“纳塔尔地区侨民,凡其原籍国迄今尚无议会选举之民选机构,不得做选民登记。”此处压根没提到印度人或亚裔人。至于印度是否有议会选举之民选机构,则由各位律师见仁见智了。不过,让我们姑且假设一下,假设1894年印度没有民选机构,今天也没有议会选举,那么纳塔尔管理选民登记的官员把印度人加入不合资格的名单,谁也不能轻易说他违法。一般而言,法律普遍假定,政府应维护民众的权力。(P.139)因此,只要当局不强烈反对,即便有此立法,印度侨民或其他人的名字也可在选民册上登记在案。换言之,如果少一点对印度人的反感,如果当地政府无意伤害印度人,即便法律条文只字不改,印度人也能做选民登记。从前面提到过的南非地区法律,我们还可举出几个诸如此类的例子。因此,明智的政府应当尽量少颁布带有阶层歧视的立法;能不颁布更好。法律一旦出台,再要撤回困难重重。国家只有在大力教化民意后,方可废除现行法律。政府若肆意修改或废除法律,国家宪政则无稳定可言,无秩序可言。
现在,德兰士瓦地区反亚裔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毒害,我们更清楚了。这些法律法规都带有种族主义特征:亚裔人因为是亚裔人所以没有选举权,而且他们在政府所划定的亚裔区外也不能拥有土地。法典中的这些法律法规一日不废,行政部门对印度人就爱莫能助。(P.140)因为它们不属一般法,米尔纳勋爵的委员会也只能另列一份清单。如果这些法律法规属于一般法,换言之,如果它们在表述上并无明确针对亚裔人,即便执行起来是有针对性,那么它们也早就和其他旧法一道被废除了。管事的官员就再也不能推诿说自己束手无策,再不能托词说旧法未被新政府立法机构废除,他们只能依法行事。
亚裔人管理局继承下这些歧视性旧法,严格执行。但凡这些法是值得执行的,政府就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堵上所有让亚裔人有可乘之机的漏洞,无论是无心之失抑或是刻意放水。问题看上去简单而直接。要么原有法律是恶法,应被废除;要么它们是正确的,但需修正其中缺陷。可是新政府却选择继续执行这些旧法。在刚刚过去的布尔战争中,印度人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生共死,但这已成了昨日黄花。比勒陀利亚的英皇代理机构曾为了印度侨民的利益据理力争,但现在改朝换代了。消除印度侨民的疾苦是英国发动布尔战争的理由之一,(P.141)但那些其言灼灼的政客目光短浅,对当地情况毫不知情。而地方官员清楚知道,原布尔政府所立之反亚裔法律法规既不够严厉,也无条理可言。如果印度人能自由出入德兰士瓦,随处经商,英国商人就会损失惨重。欧洲人和他们在政府的代表极为重视此类说法。他们蜂拥而上,只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累积最大的财富;又岂能容忍印度人分一杯羹?伪善让政治理论沦为工具,捏造合理的托词。不加掩饰的自私之辞,纯粹的商贸理由满足不了南非那些聪明的欧洲人。行不义之事的人都爱编造似是而非的理由,南非的欧洲人也不例外。史沫兹将军和其他欧洲人给出的理由如下:
“南非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而印度则是东方文化的中心。当代思想家认为,东西文明无法并存。来自彼此对立文明的人们相遇,无论人数多寡,必有冲突。(P.142)西方反对简约单纯,但东方却奉其为首要德行。如此天差地别的观点,如何可以调和?政治家需务实,无需去判断文明的优劣。西方文明或许良莠并济,但西方人皆愿一以贯之。为守住自己的文明,他们殚精力竭,抛头颅,洒热血,历尽千辛万苦。不可能让他们从此另辟蹊径。就此而论,眼下的印度侨民问题并非简单的贸易嫉妒或种族仇恨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自身文明存亡的问题,是西方文明享有自我保护的至高权力且履行相应责任的问题。或许有些公众发言人挑印度人的刺,意在激怒欧洲人;但政治思想家认为并指出,印度人本身的素质就是南非的弊端。印度人在南非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有很多世俗的品质,他们心思简单,隐忍克制,锲而不舍,精打细算。西方人进取向上,但缺乏耐性,重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好大喜功,疏于劳作,且大手大脚。故而西方人不无担心,担心若数以千计的东方人在南非定居(P.143),自己就会四处碰壁。南非的西方人并不打算自取灭亡,领袖们也不会让他们陷入窘境。”
以上是我对德高望重的欧洲名士的敦促之言所做的不偏不倚的概述。虽说他们的观点是伪哲学,但我无意暗示它们毫无根据。从现实角度而言,即,就眼下利益而言,这些观点颇有力度。只是从哲学角度而言,这些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之辞。依我浅见,公正之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改革志士也不会像鼓吹这些观点的人那样,将自身的文明摆在如此无助的位置上。据我所知,东方思想家并不担心东方文化会因东西方民族自由交往,而被汹涌而至的西方文明大潮席卷散尽。就我对东方思想的了解来看,东方文明不但不害怕接触西方文明,反而积极欢迎文明自由交流。虽然东方也存在反对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我总结出的原则,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支持此原则的例子。(P.144)尽管如此,西方思想家却声称,说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强权而非正义。于是,他们耗费时日,意欲保住自身蛮力。这些思想家亦断言,不求增长物质欲望的民族必将灭亡。西方各国移民正是奉行这样的原则在南非扎根落户,征服压制数倍于己的南非各族人民。这样的欧洲人竟会怕人畜无害的印度人?想想都觉得荒谬。之前南非的印度人就是劳工,欧洲人也没有抵制印度移民。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欧洲人对亚裔人没什么好怕的。
剩下的因素就只有贸易和肤色了。数以千计的欧洲人书面坦承,印度商人让英国商人损失惨重,而且对黄种人的憎恶已成了时下欧洲人心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在美国,虽有法律明文规定人人平等,种族歧视同样存在。像布克·塔·华盛顿 这样的黑人,就算接受了最好的西方教育,也是个品行高尚的基督徒,(P.145)彻底被西方文明同化,欧洲人还是觉得罗斯福总统不该重用他,多半今天他们还会这么认为。美国的黑人接受了西方文明,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的黑皮肤就是他们的罪,在北部各州他们被白人社会鄙夷,在南部一旦被怀疑行为不轨,便是鞭笞加身。
这样的黑人,就算接受了最好的西方教育,也是个品行高尚的基督徒,(P.145)彻底被西方文明同化,欧洲人还是觉得罗斯福总统不该重用他,多半今天他们还会这么认为。美国的黑人接受了西方文明,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的黑皮肤就是他们的罪,在北部各州他们被白人社会鄙夷,在南部一旦被怀疑行为不轨,便是鞭笞加身。
所以,读者们能看出,上述所谓的“哲学式”观点毫无实质内容。不过大家也不要认为,持这些观点的人都是伪善之徒。认为这些观点正当合理的大有人在。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没准也会提出相同的看法。在印度有句谚语说得好,凡有其行,必有其思。有人曾说过,——我们的主张不过是自己想法的反映,若得不到他人认可,我们就会不满焦急,甚至怒火中烧。
我之所以如此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不同的观点,养成理解并尊重多元观念的习惯。(P.146)要理解非暴力抵抗的理念和实践,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耐心的态度。没有这些品质,就谈不上非暴力抵抗。我不是为了著书立传才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向大家讲述南非的一段历史。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国民了解,非暴力抵抗——这个我为之生,为之奉献终身的原则——是如何产生的,了解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如何开展的;凭此认识,国民方能理解非暴力,方能愿意且能够将非暴力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