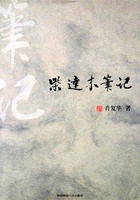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第四辑 冷湖记忆

赛什腾花
在大戈壁上的生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和生动。在1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柴达木偌大的胸襟上面,我们这个仅有五排小土屋的野外采油队只不过是五个不起眼的“蚁穴”。在这个蚁穴里,我们每天进行着繁重且危险的劳作,吃着千篇一律的粉条炖白菜、白菜熬粉条;晚上开着仿佛永远开不完的“斗私批修”会;夜里总是重温着离开北京时那锵锵铮铮的革命誓言……

作者与同学赵新安(中)、西安石油学院马迪生(左一)在前往赛什腾山的路上“指点江山”。图为当年三人在行军路上(刘勤摄于1968年5月)
就这样过去了三个月。冬季,那个能冻僵血液的冬季终于过去了,我们到柴达木的第一个春天来临了,可这里仍然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朵花。然而,春天毕竟来了,它催生着我们那颗“豪情壮志”的心之花。在那个谁都不得安分的年代,我们的心是无法安分的,同来的几个北京知青,开始策划一个“指点江山”的壮举。
西望昆仑,目不可及;北望阿尔金,隐约的雪峰虚幻飘渺,缥缈可望而不可及;东看祁连,轮廓依稀可辨,云是云,雪是雪,山是山。横亘于我们眼前蜿蜒奇峭壮观的山脊,像是祁连派生的骨骼,张开双臂召唤着我们。
队上的老师傅说:“1954年第一支勘探队来到这里时给这山起了个名字,叫赛什腾山,这是蒙语,汉语的意思是黑色的山。望山跑死马啊,这山少说也有百十来里,你们这些北京娃跑那儿去干吗?”
一个星期天的深夜,我们带上匕首、水、馒头,还找那个技术员借了个破照相机,便意气风发地向赛什腾山走去。
星光月色洒满戈壁,踩着松软的沙滩,一个脚印留下一个窝儿,像洒在大戈壁滩上的一串串花朵,我们都有一种腾空欲仙的感觉。两个多时辰过去,东方泛出鱼肚白,赛什腾山像是天地间伫立的一幅水墨画,线条清晰,泼墨凝重,黑白得当,横空出世一般。
我们立住脚庄严地迎接这日出的辉煌,因为,这个神圣的时刻,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东方红,太阳升……”这是那个时代我们心中的圣歌,每当东方红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就会升起。
赛什腾山巅像熊熊燃起的火,像积蓄已久的无限能量要喷薄爆发,整个戈壁上空的星星都暗淡,地上的砂砾都失色,大戈壁重现混沌的本色。山巅呈现半圆形火球时,天便大亮,火球真红,无法形容的红,这就是初升的太阳。
“快和太阳照张相吧!”不知谁大喊出这黎明时分的第一句话。
可我们忘记了这是摄影中最忌讳的“逆光”——“咔嚓,咔嚓”全把光明照成了黑暗,至于我们英姿飒爽、指点江山的光辉形象,更是任谁也看不清,后来我们没少骂那个“右派”技术员的破照相机。
其实,日出的时间极短,也就三四分钟,它就离开了山巅,像气球一样,升得快且高。
光明会使人精神抖擞起来,双腿顿然生风,疾走如飞,迎着朝阳,走向希望。
天呀,不远处竟出现一片大湖,碧波涟漪,水雾腾腾,时而可见莽莽丛林在雾中缥缥缈缈,时而可见炊烟缭绕的村舍隐约在时近时远,如雾中看纱又如纱中看雾,总想看个明白,恰是挡不住的诱惑,令我们几乎是小跑,投奔向大湖。
时值正午,饥肠如鼓,汗流浃背,太阳升至头顶,眼前依然是一片浑黄的大戈壁,这时,我们才清醒,是上了阳光的当,那不过是海市蜃楼。毕竟是第一次看到海市蜃楼,自然是无法抵挡奇异幻景的诱惑,我们那时正是充满幻想的年纪。
大戈壁真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大汗湿透了我们的衣服,不继续前行,毒日头会将我们烤成肉干。喝足水,吃饱馍,甩掉海市蜃楼,我们继续向赛什腾山逼近。
可是,我们不得不又住了脚。一个用盐巴和沙子垒成的灶台显现在眼前,久经风沙,它早已面目沧桑,烟筒折断,灶台里积满了沙,一峰骆驼的骨架横卧在灶台旁,像一个历史的标本。
是饥渴难耐的勘探队员杀死了骆驼以维持生命,还是饥渴难耐的骆驼自倒于这灶台前,已无法考证了。眼前,勘探队员只留下了这个灶台和伴随他们的骆驼,而骆驼只留下了这副骨架。其他,都被风沙吹走了,包括他们的脚印。
我们毕竟年轻,生存和死亡是个问题,但对我们提出这些尚为时过早,我们怀里揣着的是海市蜃楼的希望,是舍生忘死的理想。眼前的目标是赛什腾山,而那个灶台和骆驼的骨架,只是历史对我们的一种呼唤,是历史在我们心中的一种回声,让我们越发义无反顾,不计后果地向赛什腾山走去。
一个白天竟然就要过去,太阳快西落了,但大戈壁的夕阳落去要比北京晚两个时辰,此时田地依然阳光辉煌,灿烂无垠,融入其间,使人忘记自我,忘记疲倦。
当赛什腾山真正出现在我们眼前时,远远没有在远处眺望它时那般伟岸,令人高山仰止。它像一峰不死的骆驼安详平和地卧在大戈壁滩上,静观这里两千万年前大海被流放、高原被托起的历史沧桑。山不很高,我们很快便攀上了峰顶,山的那一面,迎着太阳升起的那面,铺满灿烂的金黄,可能这是每日如期而至的太阳的造化。我们突然惊喜地发现,山崖缝间星星点点迸放着一朵朵金灿灿的小黄花!小黄花,一拃来长的枝上没有绿叶,昂挺着一朵圆圆的像向日葵般的小花朵,傲然怒放,竟不觉丝毫寂寞与孤独。
我们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忘情地大喊欢呼起来,此刻那种心情,是唯有站在中国西部之西,鸟不飞、草不长,风吹石头跑的八百里瀚海才会有的切肤刻骨的感受。在北京的香山、北海、颐和园……这种单调的不起眼的小黄花可能满目皆是,谁会发神经似的为她忘情欢呼呢?唯有我们,我们来到这片戈壁,见到这小花扎根于山崖,厮守着戈壁,不能不想想自己:自己会扎下根,能与柴达木厮守多少年?一年,十年,还是一生?
该给这花命名。“红太阳”曾有诗:战地黄花分外香,就叫“战地黄花”?不好,这里也不是战地啊?那就叫“戈壁黄花”或“沙漠黄花”?也不好,它开在山崖峭壁间,干脆就叫“赛什腾花”!就像当时勘探队员初入柴达木时起地名一样,大多数人通过了,就可以列入柴达木的地图,“赛什腾花”也一定会进入柴达木植物手册的。
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束金黄色的赛什腾花。在往回走的路上,太阳彻底西落了,黑暗带来戈壁肆虐的风,天似穹庐了,把我们罩在一个大闷罐中。黑暗中,我们不能不迷路了,而且水也喝光,馒头也吃光,彻底弹尽粮绝了。
老师傅说,在大戈壁滩上迷路是最可怕的,因为大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可能围着一个点来回转圈而全然不知,你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也迷不知返,总之,直走到饥渴难耐自毙于戈壁。至今留下柴达木地图上的“南八仙”就是为怀念八名迷路献身的勘探队员命名的。
不敢想下去,唯有马不停蹄地走,用希望的能量走出浑身的热量,以不至于被寒冷冻得瑟瑟发抖。夜深了,脚沉了,肚空了,眼睛发花了……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隐隐约约看见前方有昏黄的亮光,闪烁、跳跃。
啊!原来是百十来个手电筒的光束一起齐刷刷地向我们迎来!
啊!原来是全队男女老少出来寻找我们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总难忘到柴达木后第一次探险的经历。现在想起来,闪烁在赛什腾山前那一个个菊花黄色的手电筒光束,才是赛什腾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