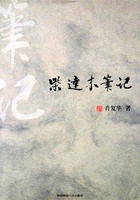
灵魂之间
那是1980年9月柴达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青海石油报》上看到石油部地质师黄先驯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黄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判了15年徒刑。那一年(1980年),石油部刚刚为他落实政策平了反。他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我们柴达木来。因为搞了一辈子石油,几乎走遍了我国的油田,唯独没有来过柴达木,这是他一直未竟的梦。他已买好了到我们柴达木的车票,却偏偏病倒在床,一查竟是癌症晚期。去世之前,黄先生要求把他的骨灰埋在柴达木,生不能来柴达木,死也要和柴达木在一起。

黄先驯,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程师、地质师,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献身祖国石油事业的人,最后的愿望是将遗骨埋葬在柴达木。图为作者清明节来看望黄先生
当时,我很感动。我从未见过黄先生,却一下子和他亲近起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对柴达木的感情。那天晚上,我写了首诗,名字叫做《冷湖上空多了一颗星》。冷湖,是我们青海石油局机关所在地,黄先生的骨灰就埋在冷湖墓地。我知道,那诗写得很幼稚,但融进了我真挚的情感:
走遍全国油田唯独未来过青海
这一来,你就再不走开
你安静地躺在冷湖的星光月下
油砂山温暖的泥土将你轻轻覆盖
倒下了,也倒在井架身边
睡下了,也睡在戈壁瀚海
最后一刻你想到的是遥远的边陲
闯进睡梦中也是石油花开……
……
那时,我初学写作,径自把诗寄给了《青海湖》杂志,没想到诗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了。事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诗是经诗人昌耀之手发表的。那时候,昌耀也被错打成“右派”刚刚平反,落实政策到杂志社当编辑。曾是天涯沦落人,又都对柴达木瀚海一片情,昌耀和黄先驯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三个人都素不相识,但心和心的相通,比彼此相识更重要,我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之间是相互感应,彼此召唤的。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清明,无论春雨绵绵,还是风沙蔽天,我都要到黄先生墓前——这不是普通人所说的“扫墓”,而是远离世俗市侩、抖落铜臭附体——净化自己心灵、检验人格尊严的洗礼。我不知道黄先生还有什么亲人,即使有,这天远地远的,也难为他祭扫。我每年都来一次,为黄先生的魂灵,更为我自己的。1990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散文《柴达木的风》,文中提到了黄先生的墓碑:
它就立在浩瀚无垠的大戈壁上,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世上恐怕没有一座墓碑会有它这样伟岸,这样宽广,无遮无拦的戈壁紧紧拥抱着它……
弹指之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偶尔在一家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黄先生的文章《梦绕柴达木,魂归昆仑西》,对他的了解更深了一层。他是湖北鄂城人,抗战期间,带着瞎母和妻小入川,然后到玉门油田,是我国老一辈石油开发者。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地质师,不过因为1957年与前苏联专家莫东耶夫关于延长油矿的地质构造的认识有异,便飞来横祸,由此深陷囹圄多年。发配他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时,儿女们曾联名给他写过一封信,求他回家团圆,因为家中已无分文收入了。可黄先生回信:“你们不要惧怕艰苦,困难和艰苦可以磨砺人的意志和品格。你们不要强迫我做我不能做的事。我不能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欺骗自己。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庭后代活着,这是禽兽都可以做到的,而人与禽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他认为符合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先驯!他为此付出了最后生命的代价,死时才六十四岁。他死时,手里还留有在狱中艰难写下的漫漫五大本关于石油的笔记,他用他孱弱的声音坚持说:“去……去……”儿女们明白了他的意思,替他说出了“去柴达木!”他这才闭上了眼睛,浑浊而凝重的泪挂在了眼角……
我无法诉说我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我也不知道如今这样用生命融进自己的理想和真理的人还有多少?我只知道我的心受到了震撼,我只想问问我自己,是否还坚持着这样的操守,而没有把高尚的对理想追求的勇气和精神丢弃在污水泥沼中,而没有蓬随风转,将心荒芜成一片戈壁沙漠?

图为作者与黄先驯大女儿黄嘉明在黄先生墓碑前
后来,我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黄嘉明是黄先驯的大女儿,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副主任。她是带着“黑五类”的帽子,含辛茹苦、靠奖学金读完大学的,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到她父亲的影子。在这篇文章中,她提到我的那首二十年前的幼稚诗和那篇短短的散文,她说他们全家如传家宝一样珍藏着它们,并感谢我、记住了我。他觉得我们虽未见过面,心却是相通的。
其实,我知道我们都要感谢的是黄先驯先生。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那我们的灵魂一定是因有黄先生不灭灵魂的点燃,才默默地息息相通的。当晚,我给黄嘉明写了一封信,寄去了一张他父亲墓地的照片。
很快,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这是我父亲去青海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从他那里来的信,我很感动……我是在办公室收到这封信的,并一口气读完,我的表情使同室人惊异,他们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心灵的震颤……”信的最后,她说已五十开外的她要西行柴达木,为父扫墓。
当晚,我又给她回了一封信:“欢迎你来,先到敦煌,然后我们同行柴达木。路虽迢迢,但有我在,就像到家一样。”
写毕,夜沉沉,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由北京开来的列车,伴我离开北京西行二十七载,我太熟悉它那绿色的车厢了。它到达甘肃的最后一站柳园时,正是深夜两点,我去接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一眼认出了她,她也一眼认出了我。我相信,如果没有灵魂之间的感应,人生中绝不会出现这样的相逢,这样的奇迹。
苍茫的夜色中,汽车驶过西征名将留下的李广杏和左公柳,穿过北魏名僧乐尊开凿的莫高窟,越过如历史长卷绵绵横亘的戈壁大漠和巍巍矗立的莽莽祁连,到达柴达木冷湖那石油井架簇拥着的黄先生的墓地时,正是太阳把这七彩的光环无私地奉献给了大戈壁……
至此,我愿长梦不醒!
至此,我们和黄先生的灵魂在柴达木相遇、相碰、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