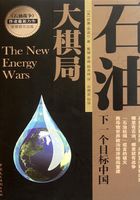
第7章 精心布棋(6)
在同一天,欧佩克阿拉伯成员国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种种罪状,宣布停止对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而荷兰的鹿特丹是西欧进口石油的主要港口。1973年10月17日,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它们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比9月份调低5%,此后每月减少5%,“直到以色列从他们自1967年6月起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像日本所说的“石油轰动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
应巴列维国王的要求,欧佩克在1973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把每桶石油的价格提至11.65美元,是之前的4倍。仅仅3个月,石油价格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令人瞠目结舌,但是纽约大银行和美英石油巨头却借此狠狠赚了一笔。
2000年9月在与笔者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沙特前石油大臣、曾任欧佩克秘书长的扎基·亚马尼王子透露,沙特国王1973年10月专门派他去德黑兰拜会巴列维,询问对方为什么非在欧佩克12月的会议上要求油价涨至每桶11.65美元,因为西方经济严重下滑对欧佩克并无好处。巴列维的回答出人意料:“回去告诉你们国王,如果他想知道答案,应该去华盛顿问亨利·基辛格。”[11]
巴列维与洛克菲勒、基辛格等美国朋友的关系非同寻常,用根深蒂固形容毫不夸张。1962年,也就是美国中情局推翻摩萨台9年后,巴列维对这帮朋友仍然念念不忘。根据其家族名下的巴列维基金会的记录,巴列维国王当年给了前中情局局长、洛克菲勒的密友艾伦·杜勒斯100万美元,给大卫·洛克菲勒200万美元,给政变一线的美国驻伊朗大使洛伊·亨德森200万美元。就连《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这个为他摇旗呐喊的商人也拿到50万美元。巴列维在1973年送给基辛格的礼物是极为珍贵的波斯地毯和上好的野生鱼子酱。[12]
1972年,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伊朗。在他的推动下,巴列维获准购买除核武器之外美国的任何武器,这个待遇连沙特国王也望尘莫及。[13]巴列维和基辛格的后台老板大卫·洛克菲勒以及大通曼哈顿银行都过从甚密。巴列维国王曾下令把政府的主要财政盈余都存进大通,1974年石油危机刚刚爆发,又下令把当月收入的10亿美元存入其账户。基辛格从政府离任后,更是马不停蹄地被招进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14]
西德——那是对手,不是朋友
1973年10月中旬,西德勃兰特政府照会美国驻德大使,声明西德在中东战争中的中立立场,不允许美国利用驻德基地为以色列提供补给。
尼克松当月30日复函勃兰特,执笔人据称是基辛格,言辞颇为犀利:
与美相比,欧洲命系中东石油。此次战争事关重大,倘若不能与美齐心协力,对西德断无裨益……所言危机事出盟约之外,援以之举非盟国之责。决然不可率意而为![15]
华盛顿不允许西德保持中立,相反,英国却可以退避三舍,以此免除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冲击。原因很简单,英国是幕后玩家,西德则不然。伦敦这次之所以能在危机中纵横捭阖,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始作俑者。其实这场阴谋原本就是针对德、日及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华尔街财团和美国政府发现对这些经济体越发难以掌控。
关于是否要对欧佩克作出“共同”反应,欧洲当时争论正酣。为避免德、法等主要石油进口国单独与中东国家建立石油贸易协定,基辛格又着手进一步干预。
基辛格建议,西欧国家和美国一道在经合组织名下建立国际能源署(IEA)。此举名义上是加强与欧洲的合作,实际上是把石油政策牢牢控制在美国手中。
魔鬼就藏在细节!
为应对能源供应的紧急事态,基辛格为国际能源署制定了章程,毫无疑问对美国格外有利,对西欧国家则不尽然。美国建立国际能源署,就是借此把欧洲能源需求的主动权死死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免欧洲单方面与石油出口国建立贸易联系,从而影响华盛顿和石油七姊妹的石油武器发挥威力。[16]
行动天衣无缝
1973至1974年,石油价格在人为操纵下上涨了4倍。为了让这场危机天衣无缝,纽约的洛克菲勒帝国、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手下的壳牌、BP等石油巨头可谓步步为营。经过15年的努力,在1973年欧佩克发起石油禁运之前,他们已把美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额提高到34%。[17]
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是1960年由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委内瑞拉五国创立的。到1971年,世界原油价格的控制权已明显从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的大油田转移到欧佩克,因为后者主导着世界石油供应。[18]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核心权力从未离开美英石油巨头半步。
一方面,欧佩克作为石油生产国卡特尔,必然依靠消费者,而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是美国、西欧和日本。另一方面,在控制石油运输、精炼及市场等方面,欧佩克需要仰仗美国,其自身安全也需要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但是,从成立到受华盛顿挑唆发起石油禁运的13年间,欧佩克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美英石油公司构成根本性的挑战。[19]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促使沙特国王下定决心禁运石油,美国和西欧因此颇受损失。接着,基辛格就让美国媒体大做文章,把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妖魔化,并指责“贪婪的石油生产国”制造了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欧佩克石油禁运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汽油抢购狂潮,提议发放配额的呼吁不绝于耳,美国经济也开始迅速衰退。欧佩克背上了“敌人”的黑锅,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却忙于吸纳欧佩克的美元盈余,在幕后乐此不疲。基辛格和索尔茨约巴登会议对此早有预见,美其名曰“石油美元再循环”,并把具体操作交给与美英石油巨头休戚相关的大银行。
1974年7月,在石油危机发生9个月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沃尔特·利维,也就是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策划此次危机的人,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外交》杂志由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对政府影响颇深,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大卫·洛克菲勒。利维在文中把矛头指向欧佩克这个新“敌人”,声称“石油生产国实际上已完全控制了各自的石油工业”。但不久他又出尔反尔,先是对欧佩克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接着又主张“石油进口国应当忍痛对石油消费进行控制”。[20]
值得注意的是,利维还鼓吹“多元能源路线”,据信也是洛克菲勒的主张,即为了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应当“制定政策减少消费,促进替代能源的开发……”。[21]他的真实目的不久便昭然若揭,其实这是筹划已久的人口控制阴谋的一部分,只是打着能源危机不可逆转的幌子而已,利维就是这场世纪骗局的急先锋。
早在一年多前,美英石油巨头就已开始密谋此次危机,并减少了自己的石油库存,以便为欧佩克的禁运推波助澜。从1972年开始,埃克森和其他美英公司就故意限制对美欧市场的石油供给。[22]为了给次年的危机渲染气氛,当权派强大的喉舌《纽约时报》在1972年4月发表了名为《能源危机即将到来》的社论,号召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愚蠢的能源消费行为……对燃料和电力采取配给制”。[23]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以为然。
石油危机不但让油价上涨了4倍,还产生了巨大的附带效应。BP、里奇菲尔德、壳牌等美英大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开发的北海油田从此变得有利可图。当然,只有在基辛格成功发动石油危机以后,这些前景不明的北海油田才有获利的可能。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里奇菲尔德和BP共同参与下,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在北极圈的加普拉德霍湾发现了当时全美最大的油田。据1974年阿拉斯加州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局的评估报告,该油田保守说也有100亿桶石油,储量超过当时具有传奇色彩的东德克萨斯油田。[24]后来,该估值又被提高到250亿桶。[25]
报告进一步指出,阿拉斯加尚有大量未探明的油田。“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可能有140亿桶储量。阿拉斯加湾的地质结构和白令海的沉积地相都表明,在该地区发现更多巨型油田的可能性很大。”[26]
与北海油田一样,要开发遥远的普拉德霍湾,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输油管道进行巨额投资,才能把石油运到加利福尼亚等地。1974年欧佩克4倍的涨价等于打开了财富之门,把这些巨型油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矿。而这些黑金的主人就是当时众所周知的石油七姊妹。[27]
基辛格大权独揽
石油危机达到顶峰的时间是1973年末,这一点很重要。那时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基辛格自然就成为事实上的总统,大权独揽“能源危机”中的美国政策。他还利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巨大权力,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情报系统。
尼克松因“水门丑闻”无暇脱身,基辛格乘机说服总统提名他为国务卿。借此妙招,基辛格或者确切地说洛克菲勒集团完全把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切刚好在“赎罪日战争”之前完成。有些华盛顿内部人士甚至认定,基辛格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的就是扩大自己的权力。
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尼克松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那样拥有无上的权力,所以他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纯属意料之中。
1973年2月,尼克松建立了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领导小组”,即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包括财政部长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基辛格总是处心积虑地确保自己处于尼克松能源政策的核心班子。尽管华盛顿和世界各地无人觉察,但一切正在按部就班地依照彼尔德伯格计划布局。到1973年初,美国原油库存已经处于警戒线以下了。[28]
舒尔茨在财政部的副手是威廉·西蒙,此人曾是华尔街券商,后被舒尔茨委以重任,担任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他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资助新保守主义的智库。1974年夏,西蒙与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会面,沙特方面强烈提议欧佩克大幅增产以抑制价格上涨。基辛格却指示国务院不予理会,巴列维也拒绝了两人的计划。按照基辛格和巴列维的意愿,油价仍旧维持在高位。时任美国驻沙特大使詹姆斯·阿金斯口无遮拦,说亚马尼深信美国或者至少是基辛格“根本没想把油价降下来”。此后不久,阿金斯就被基辛格扫地出门了。[29]
1974年初,尼克松把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派到财政部,想要研究如何让欧佩克降低油价。但这位官员吃了闭门羹,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不愿让石油降价的是银行界的大亨,他们极力主张利用高油价带来的‘石油美元再循环'牟利。这个决定错误之极……”[30]
石油价格上涨为纽约的银行业换来了真金白银,尤其是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巴列维国王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收入全部存在那里,按1974年欧佩克油价上涨后的价格,每年约为140亿美元。[31]
确保欧佩克“石油美元再循环”的顺利实施,少不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起初他在埃克森任职,后于1971年被基辛格安插到财政部。在那儿他还有一个搭档保罗·沃尔克,也是洛克菲勒的部下。他俩共同建议尼克松总统撕毁布雷顿协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改为浮动汇率。
1971年的这个决定只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序曲。实际上,关闭美元窗口正是为了在1974年把美元从黄金本位改造成石油本位。这一举动影响深远,让原本颓势的美元扶摇直上。
1975年,贝内特被派往利雅得与沙特货币局(SAMA)签订一项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装备,沙特货币局将把在石油危机中获得的大部分收益投资美国财政债券。这个协定确保了美元的强势地位,给华尔街券商带来了滚滚财源。事实上,尽管美国的工业已开始衰退,但欧佩克的石油收益充当了支撑美国世纪的财政支柱。
大卫·马尔福德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任职于怀特维德公司。贝内特派他去沙特担任沙特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指导沙特把石油美元投到正确的银行——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毫无悬念。按照索尔茨约巴登会议的安排,“石油美元再循环”计划按部就班。[32]这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大转移,华尔街和洛克菲勒集团则严密掌控着其中的每个环节。
这样一来,埃克森、美孚、德士古、雪佛龙、海湾石油、BP、壳牌在上市公司中富甲一方,年利润远超不少国家的GDP。欧佩克的石油美元利润都投到了美英大银行,像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美国银行、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然后又从那里变成贷款,借给巴西、阿根廷等石油进口国,给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